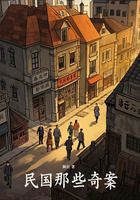
第3章 “摸金校尉”党拐子
党玉琨的“古董癖”
自古以来,总有一些心术不正之人,处心积虑地琢磨着如何发“死人财”。在他们的算计中,历代声名显赫的王侯将相、达官贵人的陵墓,便成了首要的盗掘目标。尤其是那些生前享尽荣华富贵、死后陪葬品堆积如山的帝王陵寝,更是他们绝不会轻易放过的“肥肉”。
到了民国年间,这盗墓之风愈演愈烈。许多手握兵权、割据一方的大小军阀,竟也纷纷加入了盗墓者的行列。他们日夜盘算,绞尽脑汁,一心想着从死人身上捞取巨额钱财。这样的军阀,在那个时代,还真不少见。
在众多盗掘帝王陵墓的事件中,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的大案。此案一经曝光,便如惊雷般震撼朝野,声名远播海外,引来各方人士的激烈谴责和声讨。东陵盗宝案不仅被史学家载入史册,更成为文学家笔下反复演绎的题材,传遍天下。然而,孙殿英虽名声在外,却并非军阀中唯一或第一个盗掘陵墓的。实际上,在他东陵盗宝前一年多,已经发生过一起由军阀导演的盗墓案——斗鸡台盗宝案。
那时的中国,政局动荡,战火连绵,各地大小军阀各自为政,国民政府既无力支付他们的军饷,也无法约束他们的行动。要想在这乱世中扩充实力、称霸一方,军阀们只能自谋生路,甚至不惜铤而走险。
在这些军阀中,陕西的一个地方小军阀党玉琨,便精心策划了一桩著名的盗宝案——斗鸡台盗宝案。党玉琨,陕西富平人,外号“党拐子”。他自幼不学无术,整天与地痞流氓厮混,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性格狡黠奸诈、刁钻善变,尤其嗜赌成性。他的那条跛腿,正是在一次街头斗殴中被人打伤所致。
党玉琨年轻时曾在西安、北京等地的古董店当过学徒,耳濡目染之下,对古文物有了相当的眼力,尤其擅长辨别铜器真伪。后来,他弃商从戎,投靠了盘踞在陕西凤翔的地方军阀郭坚,从一个小头目逐渐升任排、连、营、团长。由于善于钻营,他深得郭坚赏识。然而,1921年,冯玉祥整顿陕西军阀,郭坚因不服管束被杀,党玉琨失去了靠山,只得带着残兵败将逃往陕西醴泉县。
不久,郭坚的部下李寺东调,凤翔留守的军队内斗不断,四分五裂。党玉琨看准时机,于1926年率部重返凤翔,自封“师长”,号称“司令”。为了扩充实力,他深知钱财的重要性,但在国困民穷的局势下,仅靠横征暴敛显然不够。于是,他开始另辟蹊径,打起了古墓的主意。
20世纪20年代末,陕西宝鸡一带流传着一首民谣:“党拐子,土皇上,派出土匪活阎王;活阎王指挥穷人把宝挖,抬脚动手把人杀。斗鸡挖宝八个月,真把百姓害了个扎!”这首民谣中所说的“党拐子”,正是党玉琨。
党玉琨骨子里藏着一种近乎痴迷的“古董癖”。他深知文物的价值,常对手下常说:“古董乃天下之贵宝,价值连城。若以之馈赠,可讨人欢心,换得重大人情;若以之出售,足可换来枪炮弹药,助我自立为王,独霸一方。”这话从他那张满是算计的嘴里说出来,像一股歪理一样。
他对古董的迷恋,近乎病态。即便是一些破旧不堪的器物,也能让他爱不释手,摩挲把玩许久。他的师部里,常有古董商往来穿梭,有的送来消息,有的带来珍品。在他的卧室旁,专门设了两间陈列室,里面摆满了铜器、瓷器、玉器。铜器和瓷器大多是前清或民初的仿品,玉器中则有两件汉代玉璧,算是稀罕之物。至于其他,多属近代的普通货色。
党玉琨对古董的喜爱,并非纯粹出于文人的雅好。他是个野心勃勃的地方军阀,对古董的兴趣更多是出于实际考虑——他知道这些东西能换来真金白银,甚至能帮助他扩充军备,称霸一方。于是,他先在凤翔城内开设了“宝兴城”钱庄,试图借此垄断金融,聚敛军资。后来,他又勾结当地一个有名的古董商张九太,在凤翔县的灵山、宝鸡市的竹园沟一带大肆挖掘古墓,搜罗文物,以充军饷。
在他看来,掘墓盗宝是一件既省心又暴利的事情。早在他在醴泉县驻防时,曾得手三件珍贵文物:一件卣,一件簋,一件爵,上面皆刻有铭文,价值不菲。党玉琨并未将这些宝物据为己有,而是灵机一动,将它们送给了河南南阳的一个军阀。果然,对方立即“投桃报李”,回赠了他一万发子弹、两挺机枪、三支手枪。这一笔交易,让党玉琨尝到了甜头,从此对盗掘文物的兴趣愈发浓烈,手段也更加肆无忌惮。
渐渐地,党玉琨将目光投向了宝鸡斗鸡台的戴家湾。他从常来常往的古董商口中得知,斗鸡台戴家湾一带地下文物众多,几乎处处是宝,常有珍品出土。这个地方,历史上曾是周、秦王朝的发祥地,地下埋藏着极其丰富的古代珍宝。斗鸡台戴家湾的戴家沟,据《史记》记载,便是秦文公、秦宪公的墓葬所在地。早在清代末年,这里就曾出土过重要的青铜文物。每逢大雨冲刷,土崖边、田土中常常会暴露出一件件古物。当地人虽不识其来历,却都知道它们是价值连城的“宝”。
党玉琨之所以将目标锁定于此,还与一个人有关——斗鸡台的一个乡绅杨万胜。此人在乡里横行霸道,恶名昭彰。因私自加派大烟税款,激起了民愤,甚至有人扬言要将他暗杀。杨万胜惶恐不安,便找到党玉琨的亲信张志贤求情。为讨好张志贤,杨万胜透露了一个秘密:“戴家湾村后的大沟里,靠近崖壁处有几个洞,洞里有古董。村里人常去挖取卖钱,几十、几百白洋轻松到手。你若派人去挖,定能大发横财。”
张志贤将这个消息禀报给了党玉琨。党玉琨听后,异常高兴,预感到自己发财的机会来了。为了探明虚实,1927年春,他亲自前往戴家湾勘察。一番踏勘后,他确信这里确有大量宝藏。于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大规模盗宝行动,便在当年秋收后悄然拉开了序幕。
斗鸡台挖宝行动
1927年春,党玉琨站在戴家湾的黄土坡上,望着眼前这片看似平凡的土地,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他头戴礼帽,手握文明棒,身后是那辆豪华的马拉轿车,随从们骑着彩饰的高头大马,气势非凡。劣绅杨万胜早已恭候多时,满脸堆笑地将这位“党司令”迎入家中,摆下丰盛宴席,殷勤招待。几杯酒下肚,党玉琨便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询问戴家湾的“宝地”详情。
杨万胜满脸谄媚,将村子里的传说、祖辈口中的秘密一一道来。他提到村北那条深沟,每逢大雨冲刷,便有铜器、陶器露出土面,村里人曾挖出过不少“宝贝”。党玉琨听得入神,心中暗自盘算。几日后,他已对戴家湾的情况了然于胸,一个盗宝计划在他脑海中逐渐成形。
回城后,党玉琨立即召集心腹,将盗宝任务一一分派:驻扎在宝鸡县虢镇的旅长贺玉堂,被任命为挖宝总指挥;凤翔“宝兴成”钱庄的总经理范春芳,因曾在汉口古董行里摸爬滚打多年,被委任为现场总负责人;卫士班长马成龙,外号“大牙”,与宝鸡本地的柴官长、张福、白寿才等人一道,担任监工头目。此外,他还特意请来了宝鸡当地有名的古董商郑郁文,担任“挖宝先生”,负责鉴定和整修出土文物。
党玉琨的安排滴水不漏,甚至将指挥部设在杨万胜家中。每次他亲临现场,都由杨万胜负责接待,俨然将此地变成了他的临时行宫。
挖宝行动一展开,附近县区的青壮年便被强行征召而来。起初,只需附近村庄摊派,但随着挖掘面积不断扩大,人手愈发紧张。最终,宝鸡、凤翔、岐山三县的村庄都被卷入其中。高峰时,戴家湾的土地上密密麻麻挤满了上千名民工,黄土飞扬,铁锹挥动,整个村庄仿佛被翻了个底朝天。
盗宝行动一开始便取得了不小的收获。在杨万胜的指点下,开工第一天便挖出了一座汉墓,青铜器、陶器堆积如山。第三天,又一件珍贵的青铜器出土,郑郁文鉴定为“觯”。紧接着,铭文鼎、簋、戈、铜泡等文物相继现世,党玉琨的眼中满是兴奋与贪婪。
不久后,一座大墓被挖开,墓壁上绘有鲜艳的壁画:群山连绵,牛羊成群,一幅古代游牧生活的画卷跃然眼前。墓中出土的青铜器更是令人目不暇接,乌纹方鼎、扁足鼎、兽面纹尊等珍品接连被抬出。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三件铜禁,上面摆放着方鼎、尊、觯、爵等酒器,造型精美,纹饰细腻,堪称艺术精品。
盗宝的成功让党玉琨的野心愈发膨胀。他下令加强控制,增加人手,甚至不惜用极端手段逼迫民工卖命。总指挥贺玉堂,人称“活阎王”,本就残暴无情,此时更加肆无忌惮。他曾亲自下令,将一名无辜农民钉在城门上,活活折磨至死。监工头目马成龙也不是善茬,他骑着高头大马,挨村催工,对那些未出工的村民打骂罚没,毫不手软。
民工们的日子苦不堪言。他们天未亮便要出工,自带干粮与工具,挖到天黑才能收工。中午只能啃几口干粮,喝几口水,稍作喘息。晚上,外县的民工只能露宿屋檐下,挨饿受冻。监工们手持皮鞭,稍有不慎便是一顿毒打。那些因疲惫而动作迟缓的,或是因病痛无法出工的,无不遭受鞭笞与惩罚。
例如,蟠龙乡大槐树村的农民张十斤因一次迟到,就被罚大洋300元;该乡另一农民因修房一次未出工,被打得头破血流;长寿乡的杨武仅仅因为有一次未及时出工,就被关押了10天之久,直到其家人送给监工员200斤菜油后才被释放出来;为出工的事,马成龙还勒索村民韩培肥猪3头、粉条200斤。
韩家崖的农民毛谊,挖宝时在已清理完的土坑中拾了一件很小的铜器。此事恰好被杨万胜知道了,就逼他出了300块大洋,才算了事。党玉琨、贺玉堂等人还非常阴险狡诈,对民工们防范森严,措施极其狠辣,经常使民工无端受屈,惨遭不幸。
挖出来的宝物都被暂时存放在杨万胜家那里。门内,堆积如山的宝物泛着幽幽的光泽。青铜器、玉器、陶器,每一件都是党玉琨的心头好,也是他称霸一方的筹码。为了防备有人觊觎这些珍宝,党玉琨特意派了专人看守,日夜巡逻。即便如此,仍有胆大者铤而走险。
一天夜里,看守杨根满趁人不备,偷偷揣了几件宝物,悄悄溜出村子,远逃他乡。事发后,党玉琨大怒,贺玉堂更是暴跳如雷。他们怀疑到一个名叫杨冬满的民工身上。理由很简单:杨冬满曾在杨万胜家打过长工,对地形了如指掌。无辜的杨冬满被押到土坑前,贺玉堂一声令下,土水被一锹一锹地填进去,活埋的惨状令人不寒而栗。幸亏杨冬满的哥哥及时赶到,拼死将他从土中刨出,这才逃过一劫。
村民们对党玉琨和贺玉堂的暴行恨之入骨。他们编了几句民谣,唱出了心中的愤懑:“大牙来催工,鸡犬不安宁;壮年顺墙溜,老人发叹声。”还有一首:“凤翔范春芳,宝鸡贺阎王;杀人不眨眼,倾家又荡产。”这些民谣在村中传唱,却并未动摇党玉琨的野心。他依旧日夜催促挖宝,对民工的生死漠不关心。
从1927年秋到1928年7月,整整8个月,戴家湾的土地被翻了个底朝天。原本硕大的深沟被挖下来的土填平,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痕迹。为了壮大声势,贺玉堂特意请了几台大戏和皮影戏在工地上演出,连吃带喝地热闹了三个多月。村里的小吃摊、杂货铺也趁机摆满街头,仿佛在庆祝这场荒唐的“盛事”。
党玉琨的暴行终究引来了天怒人怨。他的盗宝行动不仅惊动了冯玉祥,也让宝鸡的百姓怨声载道。1928年5月,冯玉祥下令宋哲元率领第四方面军三万人马,围剿凤翔城,缴获党玉琨盗掘的珍宝。
宋哲元兵临城下,对党玉琨的守军发出警告:“我给你们三天时间,降或守,自己选择。”
三天后,战事打响。凤翔城坚固异常,宋哲元猛攻两月仍未能破城。无奈之下,他请调张维玺的主力十三军增援。最终,宋、张二部合力,用爆破手段炸开城墙,才攻入城内。巷战短暂却激烈,党玉琨在城东墙下被击毙,其部众也被悉数遣散。
党玉琨的宝物,一部分摆在他卧室的万宝架上,另一部分藏于二姨太张彩霞的房中,最重要的器皿则被存放在秘密库房,由卫兵严密看守。宋哲元攻破凤翔后,这些珍宝尽数落入他手中。
1928年9月,宋哲元将珍宝在西安新城四面亭军部展览一天,供部下观赏。随后,他令军法处长萧振瀛带兵押送宝物至西安军部。这些珍宝的命运,也自此开始了戏剧性的流转和散失。
运抵西安后,宋哲元先是请芦真照相馆的摄影师为每件珍宝拍照,又请文物鉴定专家薛崇勋逐件鉴定。他将一部分珍宝送给了上司冯玉祥,其中一件水鼎后来由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其余珍宝,由宋哲元的小妾和萧振瀛带到了天津,存放在英租界的家中。再后来,通过天津的古董商,这些珍宝中的一部分被卖给了外国人,流落他乡。
无数珍宝流落海外
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未治在《东方学纪要》一书中说:“宝鸡出土的铜器乃是在纽约的中国古董商戴运斋姚氏(叔来),从天津买来。姚氏说,党玉琨在宝鸡盗掘的铜器首先归于冯玉祥之手。又闻,曾为波士顿希金氏藏的告田觥(现藏香港),也是通过在纽约的日本古董商购自天津。”
在这段话中,除了将“宋哲元”误为“冯玉祥”外,其他内容都是确凿可信的。由此可见,党玉琨所盗得宝鸡斗鸡台的珍贵文物,实际上大部分是由宋哲元及其手下萧振瀛运抵天津后才开始流失出去的一些包括现在在美国、日本、英国及香港的宝鸡斗鸡台珍宝,大多是由此而流失海外的。这使祖国的珍贵文化遗产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当年在对这批文物做鉴定时,颇为细心的薛崇勋曾经用墨汁拓了数十张纸的铭文拓片。铭文大都在1至3字,最多的10几个字。当宋哲元调离西安时,这批文物照片和珍贵的拓片资料可能没被带走,后来被一农民在西北关发现。
这些珍贵的资料被装订成五本册子,像字帖一样精美装裱。它们在西安的古董市场几经辗转,最终被一个名叫王子善的古董商收入囊中。1945年,刘安国在北大街的破烂市上偶然遇见了王子善,他正拿着这五本照片册出售。刘安国一眼认出其中的价值,通过王子善之子,将册子买下。
刘安国得到册子后,立刻请古董名家杨钟健过目,并找到薛崇勋鉴定。薛老先生翻开册子,看到自己当年亲手拓下的铭文,不禁感慨万千。他在册子卷首写道:“彝器景本五册,乃富平党毓坤驻凤翔,迫发民夫在斗鸡台发掘者……去今已十五载矣。”
刘安国深知这些资料的重要性,他将其中的铜器整理成册,撰写了《雍宝铜器小群图说长编》,并托人带到北京,请故宫博物院的唐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陈梦家等专家过目。然而,因种种原因,这些资料未能出版,最终原物退回。
“文革”期间,刘安国和薛崇勋的家遭到抄检,这些珍贵的拓片和照片再次遗失。直到粉碎“四人帮”后,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这些资料才在考古专家们的努力下重见天日,并在《中国文物报》上陆续刊出。
关于党玉琨在斗鸡台盗挖的墓葬数量,众说纷纭。有人说是上百座,有人说是几十座。新中国成立后,文物考古工作者通过深入调查和多方查证,最终确定,党玉琨所盗掘的古墓葬至少有五十多座,挖出的铜器、玉器等文物约一千五百多件。其中保存完好的有七百四十多件,资料完整可做研究的有153件。这些文物的所属时代跨越商、周、秦、汉,其中的西周早期铜器尤为珍贵。
在这些文物中,有饪食器七十件,酒器三十九件,水器九件,工具两件,兵器十八件,以及其他杂器。
除了这些文物,1927年12月,宝鸡斗鸡台还挖出了一个巨大的车马坑。坑内,马骨架完整,车饰品、马饰品散落在四周。这车马坑,本应是西周初期车马构造的珍贵研究资料,蕴含着周代礼制的秘密。结果,党玉琨的贪婪与野蛮,让这一切化为泡影。
这些被党玉琨挖出的青铜器,不仅仅是专供研究的文物,更是一个个璀璨的艺术品。其中一件“禁”,尤为引人注目。这是承载酒器的器座,古代礼制中的至高存在,只有国家、王室才能使用。这在历史文献中虽有记载,但在考古发掘中却从来未见实物出土。清光绪二十七年,斗鸡台发现第一件铜禁,后落入清末重臣端方之手,最终流入美国,现存放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另一件夔纹铜禁的命运却更加曲折。它在天津隐匿了将近40年,直到1968年,天津市文物管理处根据传闻找到了它。
这件禁,属于西周早期,被发现时藏在宋哲元之弟的小妾王玉荣家中。抗日战争期间,宋哲元去世,日本人抄家带走诸多珍宝,宋哲元的弟弟却通过种种手段,将铜禁从日军手中夺回。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而来,王玉荣将铜禁藏于房屋夹层中,这才让它免于毁灭。如今,这件孤品,经故宫博物院专家修复,静静陈列在天津博物馆,供后人瞻仰。
这件夔纹铜禁高23厘米,长126厘米,长方形,四周镂孔,饰两层夔纹。禁面上三孔,中孔置卣,右置觥,左孔置物已不可考。但这件禁,仅仅是党玉琨当年盗掘的三件禁中最小的一个。另外两件禁,高约60厘米,长126厘米,宽70厘米,禁面置有两排酒器,四周饰三层夔纹。可惜,这两件珍宝至今下落不明,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之中。
党玉琨的盗掘不止于此。他还曾挖出一个大墓,墓壁上绘有壁画,大山、牛羊、大路、生活用具,画面古朴而生动。墓中出土的青铜器众多,乌纹方鼎、扁足鼎、兽面纹尊,每一件都承载着历史的重量。乌纹方鼎上刻有铭文,详细记载了周公东征归来后的祭祀活动,因而被称为“周公方鼎”。可惜,这件极具历史价值的方鼎也被盗往国外,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党玉琨盗掘的珍宝,很大一部分流散海外,至今仍有许多器物下落不明。仅有少数几件幸存,分别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宝鸡市博物馆。而那些被毁灭的文物,只留下100多张图片,成为研究的珍贵资料。
党玉琨为了安全,将盗掘的青铜器全部运往凤翔大本营藏匿,并派人邀请考古专家党晴梵前来鉴定。可惜,党晴梵当时卧病在床,未能到场。解放后,他回忆起此事,依旧惋惜不已:“致令富有历史性之宝物,交臂失之,殊觉遗憾不少。”
党玉琨的盗掘毫无章法,甚至对陶器、石器等文物不屑一顾。工人们在挖掘时,一旦发现陶器,要么随手打碎,要么弃之不顾。而参加强迫劳动的农民们,既不懂文物的价值,又心怀不满。他们故意破坏文物,以发泄心中的愤懑。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曾考察斗鸡台,感慨道:“陕西地下如仰韶期之红陶、灰陶,虽不少概见,而带色陶片,在考察范围内尚不多有。而斗鸡台却因前数年党玉琨之挖掘毁弃,地面上石器碎块,带色陶片都时时可见。”这番话,不难看出党玉琨盗掘对文物破坏的严重程度。
党玉琨斗鸡台盗宝案,是军阀混战时代的缩影。其盗掘规模和文物价值,几乎可与孙殿英东陵盗宝案相提并论。然而,党玉琨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军阀,他的罪行并未引起太多关注。此次盗掘对象是数千年前的帝王陵墓,与东陵盗掘清朝皇室陵寝相比,显得更加隐晦。正因如此,这场盗宝案的悲剧,更像是一场无声的浩劫。
并且,这场盗宝案造成的灾难是双重的。它让当地百姓饱受苦难,也严重破坏了国家的文物宝库。党玉琨的贪婪与无知,让无数珍贵文物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给祖国的传统文化遗产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