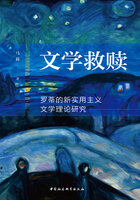
第5章 《新实用主义文学缘起》:罗蒂其人
罗蒂是居于欧洲大陆哲学与英美分析哲学之间的新实用主义哲学家,他不仅继承了美国哲学的主流传统,也体现了当代主流哲学思想,同时兼收并蓄了欧洲大陆哲学诸要素和19世纪浪漫主义的传统,呈现出令人瞩目的“合流”趋势。[8]本章主要介绍罗蒂由哲学到文学的学术思想发展历程,探讨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来源,尤其是与文学思想相关的内容,主要解决罗蒂的文学思想溯源问题。
理查德·罗蒂(1931—2007)是当代美国极具影响力的新实用主义哲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出身的罗蒂,研究兴趣广泛,其研究涉及哲学、政治、文学艺术、宗教、伦理、文化等诸多方面,是当代西方哲学界与文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罗蒂出生于美国纽约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家庭,家中往来的哲学家对幼年时期的罗蒂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杜威(John Dewey)、胡克(Sidney Hook)等哲学家都曾是罗蒂父母家中的座上客。他14岁进入芝加哥大学哲学系,18岁获得学士学位,21岁获得硕士学位。芝加哥大学是杜威早年创立实用主义芝加哥学派之地,在这里,罗蒂受到了当时最好的正统哲学熏陶。他曾师从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人物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杜威的学生麦基恩(Richard Mckeon),并在怀特海(Alfred N.Whitehead)的弟子哈特肖恩(Charles Hartshorne)的指导下完成了研究怀特海“永恒客体理论”的硕士学位论文。1953年至1956年,罗蒂进入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韦斯(Paul Weiss)指导下研究怀特海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这一时期他的授业恩师与芝加哥大学时期非常相似,逻辑经验主义哲学家亨普尔(Carl G. Hempel)取代了卡尔纳普,韦斯替代了哲学史家哈特肖恩,布鲁姆鲍(Robert Brumbaugh)代替麦基恩,[9]因此实用主义和哲学史研究对罗蒂的影响得到了延续和深化。得天独厚的家庭环境、丰富的学习经历、系统的哲学训练、勤敏好思的个人特质使得罗蒂与同时代的其他美国哲学家相比,知识背景更加宽阔,思想来源更为丰富,其文学思想正是熔铸在深厚的哲学底基之上。
受哈特肖恩的影响,罗蒂曾经迷恋形而上学。他在15岁至20岁的青年时期曾立志成为一名柏拉图主义者:相信苏格拉底(Socrates)的善即知识,梦想着能够抵达柏拉图(Plato)“分界线”的顶端,“超越了各种假说的某个地方”,在那里真理的光辉能够普照得到了升华的、聪明而善良的灵魂。当时的罗蒂向往着借助于某个思想框架或者审美框架达到像诗人叶芝(W. B. Yeats)描述的那样,“在单纯的一瞥中把持了正义和实在”[10]。可以说,1960年之前的罗蒂只对哲学史和形而上学感兴趣。[11]遍读哲学典籍之后,罗蒂对基础主义和确定性的追求虽然以彻底的失败告终,但是却夯实了他以哲学为业的事业底基。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罗蒂在芝加哥大学以及耶鲁大学进行专业哲学的学习时期正值卡尔纳普、亨普尔、塔斯基(Alfred Tarski)、赖辛巴哈(Hans Reichenbach)等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统治美国大学哲学院系的黄金时代。求学时期的罗蒂浸沐于逻辑主义哲学之中,却始终对其不感兴趣,这些德奥移民的科学哲学家的反历史倾向和试图把哲学科学化的做法遭到罗蒂的反感。因此,这一当时哲学界的主导潮流非但未被纳入罗蒂的哲学框架,反而成为罗蒂抵制以科学理性为政治道德文明范式,追求浪漫主义诗性文化的动因,为罗蒂从哲学转向文学埋下了伏笔。
博士毕业之后,罗蒂曾短期留在耶鲁大学任教,后于1958年至1961年供职于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哲学研究》曾将罗蒂的兴趣吸引至分析哲学领域——1961年罗蒂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哲学系讲师,并在这个分析哲学的重镇任教21年。这段时期又可以划分成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罗蒂热衷分析哲学,他在1967年主编的《语言学转向》一书中发表长篇导言“语言哲学的元哲学困境”,在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奠定了他在分析哲学领域的坚定地位;而从20世纪70年代起的后一阶段,他开始质疑这种哲学的根基和目标[12],逐渐显露出超越分析哲学的倾向,成为分析哲学的“叛逆者”[13]。罗蒂批判分析哲学家的研究艰深晦涩且各自为政,他们的研究由于过度强调专门化和技术化而难以互通,始终没能发展出一个超越代际的问题域。正是在这第二个时期,仍然在普林斯顿,罗蒂首次遇到了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后者引导他重新审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启发他返回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并发现杜威、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之间的相似性。此后,罗蒂在1979年出版他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体系性哲学专著《哲学和自然之镜》,以分析哲学的论证手法否定传统镜式哲学,构思哲学的未来形态,正式宣告对形而上学传统和分析哲学的反叛,逐步走上了“后哲学文化”和“文学文化”的建构之路。书中对传统认识论哲学的综合性批判立场、人类及文化平等对话的哲学观点掀起轩然大波,在美国哲学界褒贬不一,引发了支持者和反对派的唇枪舌剑。
1982年罗蒂离开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赴弗吉尼亚大学担任人文科学教授,这可以视为他由哲学转向文学的第一次转折点。在同年发表的论文集《实用主义的后果》中,他首次提出“后哲学文化”概念,决意挑战“大写”的真理、哲学的意义,站在分析哲学的外部对文化展开反思。任教弗吉尼亚大学的15年中,罗蒂陆续出版了《偶然反讽与团结》(1989)、《客观性、相对主义与真理》(1991)、《海德格尔及他人研究文集》(1991),这些哲学专著均以论文集形式出版,多是集结他的讲演稿或与其他哲学家进行哲学论争的文章。论述的焦点及论述的语言风格都与追求科学化的哲学迥然不同,越发趋向欧洲大陆哲学。非技术化的语言有助于罗蒂哲学思想的广泛传播,[14]对文学的青睐使他的哲学反思突破了传统哲学思维框架的束缚,反对哲学之王、科学之王,尊崇文学的思想在罗蒂的著作中越发清晰。
1998年,罗蒂担任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彻底实现从哲学系到文学系教授的转变,此时距他生命的终点仅剩9年的时间。同年出版的《真理与进步》《筑就我们的国家》,以及随后出版的《哲学与社会希望》(1999)、《文化政治哲学》(2007)中清晰地显露出罗蒂晚年对政治、文化、幸福等实用主义话题的关注。
2007年,罗蒂辞世。某种程度上,作为哲学家的罗蒂在文学系教职上为自己的学术和生命画上了句号,这种结局在哲学家们看来也许颇具讽刺和悲剧意味。背弃分析哲学,转而推崇文学、政治、文化研究,使罗蒂在美国哲学界被排斥在分析哲学主导的主流之外,成为正统哲学领域的边缘人物。在文学领域,研究者们对罗蒂及其新实用主义文学思想奉若至宝,对其文学思想内涵、价值与意义的探索正日益升温,以其文学思想为抓手进行文本分析的尝试方兴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