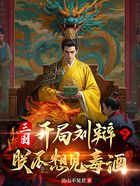
第1章 奸贼,忠臣?
中平六年八月戊辰,晌午。(公元189年8月25日)
洛阳北宫禁门,这片素来象征着天家威严的帝后寝居区,
往昔即便是权倾朝野的大将军何进,欲入此门亦需临时请旨,
而此刻这禁门所在,却被嘶喊声、冲门声、厮杀声所淹没。
……
“宦官谋杀大臣,大将军何进为阉竖所害,快……速速杀入宫去,诛杀恶党!”
“羽林军何在?快行调度至禁门护卫,否则吾等命今日必休矣……”
伴随阵阵喧嚣杂乱声,整个北宫之内如今早已人心惶惶,人人忧色难掩。
值此淆乱之际,在北宫地势最高处的温德殿内,
却有一人神色茫然,别说忧扰,此时甚至于对宫中变故都一头雾水,疑惑连连。
……
“这是何处,为何我在这里……”
刘卞此时正头疼欲裂,耳边传来内侍们哭诉国舅被十常侍所杀的声音,但他却无暇顾及。
此时低头看向铜镜,只见镜中映出一张十七八岁的少年面孔,英气逼人。
“我不是在夜读昨日从旧货摊淘来的孤本《旧汉书》吗?”
当他思及此处时,脑海却不断梳理着两份截然不同的记忆,
在过了好半晌后,刘卞方才舒展眉心,如梦初醒状喃喃自语:
“原来我穿成了东汉末年的少帝刘辩吗?”
但这皇帝之位在本朝本代可不是什么上天垂怜的大喜事……
作为前世历史系博士的刘辩这点常识还是知道的,
如今天下动荡,年景非太平,就连自己这位少帝也端不是什么英姿之主……
“照此来看,这般开局倒还真成了降大任前的苦其心志,也不知哪位大能在考验自己……”
想到此处,刘辩晒然一笑,不禁用力的揉了揉眉心。
但好在穿越之后,自己居然如同开窍一般,
前世本来所学庞杂的历史知识,
此时却在脑海中若走马观花,甚至可以做到过目不忘,
刘辩有种自信,单凭如今的记忆力,放在后世有科举之年,只要稍加勤奋,
不说殿试三甲这种高难度挑战,那起码混个进士出身倒却也不难……
但刘辩还没来得及欣喜,
反倒是因如今记忆太好,
竟兀自在脑海中回忆出一段前世所看史书对这位少帝的评价:
“皇子辩轻佻无威仪,不可为人主……”
.......
“脏,着实骂得太脏了。”
也不知是否因已有代入心里作祟,
此时刘辩,心中莫名不忿,兴致全无。
好一个不可为人主,那我穿越意义何在?
且说不就因自己继承了祖宗风仪甚伟的容貌,就要被人诟病为轻佻。
至于无威仪不可为人主,更是扯淡之言!
十八岁的年纪就要有帝王威严,
写此言者何不找找自己的问题,为何人家都居庙堂之高,
自己却一把岁数却还有闲工夫在这写史……
不过骂归骂,但刘卞心下明白,
自己前身的结局却是绝不存伪,毫无质疑。
废帝,鸩杀……
就连自己死后都不安生,被葬于宦贼中常侍赵忠墓穴旁,
真可谓是极尽羞辱!
那既然穿越至此,总不能还与前身一般,靠着寄人篱下坐等死路,
自然要敢于任事,负艰大之业,不然岂不是太对不住此次莫名的天降大位,神器天授……
刘辩不禁在脑海动些心思,试图找找如今有何破局之策。
如今是八月戊辰(8月25日),
而记忆中董卓却是在癸亥日(27日)才从十常侍张让等人手中,将自己“迎”回宫来。
那据此看,董卓起码离率兵入洛京还需两日光景,
那现下还是有机会可以苟全性命于乱世……
那如今局势,到底该如之奈何?
自己前身最大依靠常自诩“我掌天下权”的舅舅何进遭诛,
导致自己这个幼君,在这禁宫中可以说是毫无根基,政不由己出,
那既如此便不得不先寻个死忠汉室之人扶持,
但至于是何人,
还待自己先过眼下即将被挟持逃往邙山这道难关再做考量……
起码这一世自己可不想再听到什么,
“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走北邙”这种有所损汉家威仪的民谣。
待刘辩理清思路后,便正了正此时身着的赤黄绛纱袍,
拿住了一副正襟危坐的架子,举止亦十分合乎礼制,似为迎待某人做好准备。
“这前身虽好玩乐,但这装模作样的礼仪功夫却没落下……”
感觉身体熟悉无比的肌肉记忆做出如此姿态,刘辩不禁莞尔一笑。
……
而不过俄顷后,殿外便忽而一阵急促慌乱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且听其拖沓声来者应该甚众!
“终于来了吗?”
刘辩听着脚步已经大概猜到,在此混乱之际有谁还会特意来寻自己,
等来众推开殿门,
便见由一年逾六旬,眼神阴鸷的老宦官领衔,
身后数位提刀按剑的太监、侍从亦步亦趋,直奔刘辩而来。
刘辩眯眼望去,
根据之前的记忆,为首的不正是如今内臣中最为显贵的人物,十常侍之首张让吗?
这张让虽不如后世刘瑾、魏忠贤这种权倾朝野的大宦官出名,
但恐怕单论地位而言,在历朝太监中应是数一数二。
毕竟在此之前可从未出过让皇帝都称阿父的巨宦,可见其何等猖獗。
“陛下!事情紧迫,快随臣等出宫,那帮外贼如今欲要害我们君臣二人性命……”
然尚未及张让等人持刀进殿门,刘辩便闻一声尖声高喝,
至于之前那几位还在哭诉,想在皇帝面前诉点衷心的贴身内侍,
一见平日内见面都要恭声喊着老祖宗的声音,
早就做鸟兽散去,哪还顾得上这位年纪轻轻的少帝?
见此情景刘辩也是当下愕然无语,你们好歹也撒些眼泪,道几句先去寻人救我,
待日后我若起复也能记你们个几分好处不是?
殿内此时此刻,也只余下刘辩与张让一群宦臣,气氛显得十分凝重,剑拔弩张。
但如此一来刘辩倒反而有机会细细打量如今张让一眼,
张让此时虽身着朴素,不复平日蟒服在身的显赫模样,
应是方便之后逃难才作如此打扮,
但即便这遭难之际,也仍可见其唇角微垂,难掩平日的官威如海,
“不愧是能坐上十常侍之首的人物,数年来谋划数次党锢,
力压士族清流数十载,光凭这幅气势就可见其平日多跋扈……”
刘辩在心中默道一声,
而就在张让等人快到御前之际,也不禁扫了眼如今正襟危坐的少年皇帝,
不由得心下一凛,
“皇帝怎省得与从前神情姿仪判若两人?”
在张让等人的印象中,这位胆怯的少帝,
不应该早就躲进某个隐蔽之所,或在何后怀中寻求庇护……
但事有紧急,张让也顾不得多想,
也不待刘辩是否听清,予以以回答,
就使了使眼色让手下先行绑走刘辩再说,丝毫不掩饰其如今的挟持之意,
“图穷见匕,如今到连敷衍都不敷衍了。”
刘辩看着这群拿刀提剑的内宦们,
突然莫名有些表演欲望冲动在心底跃跃,表面不露声色,
装出一副阴沉模样怒声喝止道,
“放肆,朕乃大汉天子,若是朕不从你等,那张让你今日便要弑君吗?”
刘辩声大且愤慨,当场就吓住几位已经快步向前欲做拉扯状的年轻宦官们。
此言是刘辩在张让等人来之前就想好的措辞,
是故意不予张让等人以劫帝为借口,反而率先扣上一个欲弑帝的大帽的下马威。
这两个乍一听似乎没有多大区别,其实讲究很大,
原因在于张让是宦官,且是那种并非完全掌握兵权的宦官,
这类宦官最多无非是擅权而已,绝不能弑帝,
他们自身的权威都是皇帝默许罢了,
离了皇帝,想要他们命就如曹操所说无非一狱卒即可。
宦官们眼见如此,便一脸为难转头看向老祖宗,示意是否继续“护帝躲贼”……
“陛下,毋要多想,有外贼领兵入宫,臣无非是以圣体安危着想……”
张让此时亦面无表情,故意不同与紧盯自己的刘辩对视,
内心却更讶于少帝如今竟变得如此沉稳,
居然不复当初无有母后在侧便懦弱无刚之相。
但张让话未言罢,便被似笑非笑的刘辩兀自打断,
“你们借我母后诏国舅入宫之际,擅杀了国舅,
真当无人知晓,还欲把朕当愚昧孩童糊弄?”
“如今尔虽势众,但朕今日早已下定决心,宁死不随你出宫,你若强逼朕,
今日无非皇帝死社稷而已!
而大将军麾下诸将亦破宫门在即,尔等若再纠缠,必死无疑……”
语罢,刘辩缓缓拔出之前用以防身宝剑,
与张让等人成对峙状,眼神凶狠要杀人……
张让见状,心中惊疑不定,顿了顿,面色更为阴沉,但还是开口解释道,
“不管陛下信与不信,臣无有过弑帝之心……”
张让此言一出,与之同行,一脸情急的段珪忍不住插言道,
“张公,如今事从紧急,何故多言,若陛下强掳不得,我们自走便是……”
听到段珪提醒,张让恍然到情急之下居然被这小皇帝说的有些失了方寸,
眼看当下刘辩态度如此决然强硬,权衡之下强求不得,自己又不能发狠做弑君之举,
见状,张让内心盘算一番,便当机立断,准备舍了皇帝不要,
先带着余下心腹从北宫夏门出先逃至邙山一带再说。
然而,就在张让转身之际,刘辩却忽然缓缓开口,
“阿公,如今世家豪族无不欲置你于死地,
即便你逃至邙山,虽可暂避,但两面环水(洛河、黄河),实为“死地”耳。”
“陛下怎知臣等欲逃往邙山?”
张让如此情境下这声阿公,难免心神震荡,实感意外,自灵帝薨后,已经很久未听刘辩如此称呼自己,
“如今你若想走出洛阳无非三条路,
一则西逃函谷,投奔董卓,但路途遥远,此时前往实属不智,
二为东走虎牢,去你发家之地,但途径关东,世家在此经营数百年,你去此必遭擒获。
唯有这邙山扼守洛阳北门户且为先祖皇陵,
你尚可借裹挟我之势,以护帝谒陵之名,静待时局变化,是也不是?”
此言一出,若平地惊雷,
在场包括张让,段珪之内所有在场之人都面面相觑,
之前宫内人人皆私下传言这皇上昏懦不纲,
与质帝相仿,以后必是个可欺之君,
如今看来大谬矣,光凭如今胆气,也当得讲上一句有光武遗风不是?
“那陛下既出此言,何以教我?“
张让面色复杂,转回刚准备离开的身子,缓缓问道.
“其实如今阿公去往何处都难逃一死,辩亦无良策,但我有一言,乃诚望阿公听之。”
“陛下请言。”
“现如今,诚愿阿公自绝与此,一来不负先皇厚遇,对你知遇之恩,
二则我须借阿公头颅以示众耳,安天下人之心。”
此言一出,除张让,段珪外所有人都心中疑道,
这陛下是在此梦呓不成?
否则怎会在此等境遇还说此等胡话。
“陛下,如此之言,可否再给老臣一个自绝于此的理由。”
听闻刘辩如此恳切,让自己自决,张让听后没有动怒,
反而面色平静回道,声音听不出任何情绪,
“张公不可……”
旁边段珪与张让共事多年,再加上宦官本就擅长察言观色,
听到张让如此反常的语气,和故意负后却掩不住有些微颤的双手,
哪里还不知张让心中主意,正还欲再劝时,
被张让一个凌厉的眼神瞪了回去,
气的段珪在旁,眼眶泛红,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
“我常闻先帝说阿公忠心,但我亦知你有祸主乱政之举,
阿公可谓是负尽天下百姓,就连豪门权贵也欲除你于后快,
但辩扪心自问下,却只得坦言你张让唯独不负我天家这一家一姓,”
“若无你外制所谓世家清流,这天下我刘家早已坐不妥当,
如今大将军入宫诛杀你等,无非是被那世家如袁氏,杨氏等借了刀罢了。”
“至于逃窜于邙山一脉你能想到,他人怎会不做此想?”
“河南中部掾闵贡素为骨鲠之臣,若知你逃窜,必率兵沿邙山南麓把守”,
“阿公如今横竖一死,我如今可谓无权无势,保不下你,
唯借阿公头颅一用,方可安天下人之心,再徐徐图之,”
“且我曾听闻阿公收养一子张奉,辩虽不敢尽言,但会试着勉力保之,
让你张家不至于留不下一个续香火之人,阿公且看如何?”
耐心听完刘辩所说后,张让不禁长叹一声,
不曾想过少帝对周遭地理如此熟稔,也对人心有如此揣摩,
刘辩所说正是戳中他心中一直担忧所在,
和之前十常侍几人对着舆图商议时结果大差不差,
这位素来注重威仪的巨宦,想通后不由得彻底失了心气,
居然当起众人面,不顾形象,突然放声大笑,
“那就固陛下所愿,陛下都帮臣后路安排的明白,做臣下怎能不从……”
段珪却等人闻此言者皆恍惚失神,骤然大惑。
“张公你怎能……”
张让却置若罔闻,
“咱家不求你们如何,若不信陛下言,你等自求活路去罢。”
刘辩在旁也不语,只是一味盯着张让一人。
其实刘辩之所以如此说话,也是在赌运气,是根据熟悉历史走向来反推人心,
这张让前世挟持自己至孟津,被重兵包围之际,
没有来拉着自己陪他一同跳河,反而是说了一番忠心可见之言后,自顾投河而死。
那既如此,自己先摆明你无论去哪都是死路一条,
彻底断了张让后路,这样逼得张让不得不临死前卖个好予我罢了……
段珪此时看着这位共事多年,亦父亦师的同僚,咬牙犹豫片刻,终于还是觉得性命要紧,
“张公你且保重,我等还欲谋条活路……”
说完也就不顾两人,径自领着余下人匆匆退至皇宫复道。
眼见殿内又只有两人之时,张让终于昂头迎上刘辩目光,看着刘辩如今英气模样,
突然颔首笑道,
“陛下,你可否再与咱明言一句……”
张让言语间也不再称臣,换了个亲昵称谓。
“阿公请讲。”
“咱自小看着陛下长大,陛下如今还是陛下否……”
“深宫内院,若无隐忍之功,岂不是秀木于林,风必摧之?”
“那如此看陛下果有高祖遗风,咱之前还常恐,
臣等若是殄灭,天下必乱矣,如今看来咱可去地下常伴先帝矣。”
语罢,张让便摘下头上所系方便逃亡的青帛,放置一旁,
披头散发,朝向灵帝陵寝方向,一叩三拜后涕泪横流,随后又咬牙拔剑道,
“咱柔弱,被先帝保养太好,如今早已受不了那刀风霜剑的,唯有去地下侍奉先帝才算舒心,
其实咱亦知陛下并非真心,但我本没落世家,朝夕可死,
奈何先帝厚恩,让我这等残缺之人苟活至今,此恩咱不可不报……
如今让仅唯愿陛下能雄武英明,让我大汉壮哉若从前,再无有臣子敢有乱上欺君之举……”
张让此时声音无比尖细,但却显得十分决然,像是回忆起什么往事一般。
语罢,便拔剑抹脖,不见丝毫犹豫之色,
大汉中常侍,张让自此便自刎于这取名自“色思温,克明俊德”的温德殿内……
巨宦者,须内极克己,外峻刑名,
看着这位为自己而死的宦官,刘辩不由得叹了口气。
其实方才所说之言,大部分为刘辩内心真实所想。
刘辩读史多年,对如今局势看的明白,
无非是那群氏族豪强,见张让等人动了自己的利益,
眼下故意借何进这个新晋权贵之手,召令诸将士入宫诛杀宦贼,
同时诏曾受汝南袁氏大恩的董卓,丁原等外兵入京。
若说张让等人不忠,乃至后世史书上隐约意指张让等人曾勾结黄巾,
这方面刘辩是一点不相信……
换而言之倘若自己深受圣眷,手握朝纲,
反而去与一群造反的贼寇相勾结,企图推翻大汉,
真还把张让当成农民起义的精神领袖不成?
那此何解?
无非便是世家执笔,栽赃嫁祸罢了。
话又说回来,倘若张让等人不死,那还会有后来的董卓乱京吗……
刘辩缓步走下台阶,到了这位已死宦官身旁。
默道了声得罪,在数次欲呕的情况下终于割下张让头颅,踉踉跄跄走到殿前。
此时何进麾下众将已攻陷城门,
刘辩才至殿前就望见远处有一老将,满身血污,手持长戟匆匆赶来。
来人刘辩认识,正是尚书卢植。
卢植曾于宫中授过刘辩经传,两人之间本就熟识。
待到近前,卢植眼见刘辩手拿张让头颅,内心甚惊,刚欲下下拜,问帝是否无恙。
却被刘辩单手扶住。
“卢师且慢,如今我身体稍有不适,先快遣人救下二国舅何苗,再将扶我至人多处,我有要事要宣。”
卢植闻此言,虽心下百般存疑,但还是点头称诺,
卢植虽是经传大家,但亦领兵多年,素来雷厉风行,
眼见陛下如此吩咐,便亲自搀扶着少帝,让数位士卒在前率先开路,
刘辩便在众士卒拥簇下,
片刻功夫就到了某殿最高处,
望着尚在屠戮内宫宦官的将士们,
刘辩腹中作呕感已稍有平复,深吸一口气后,
便左手凭栏,
右手使力将张让头颅高高举起,用尽全身力气对着阶下沉声高喝,
“宦首张让已授首,诸将士毋再慌乱,停止杀戮,各自归营,关押有罪之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