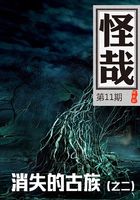
第4章 并未消失的契丹后裔(1)
一
1922年6月,一个炎热的夏日,在内蒙古巴林右旗,一位名叫克尔文的比利时传教士,在一座早已盗掘一空的古墓石碑上发现了一些类似文字的符号,它不同于当时已知的任何文字,形如天书。
对照了陕西唐乾陵前《无字碑》上的《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他们确认那是辽国第六位皇帝辽圣宗耶律隆绪的陵墓。不过,当时,专家们认为,这是女真文。直到1925年,日本京都大学羽田亨教授才撰文指出这一错误。
十年后,中国学者罗福成、王静如和厉鼎奎等确认了庆陵石碑上的文字乃是消失已久的契丹文。他们从庆陵哀册和《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入手,释出了庆陵哀册的标题,还有年号、干支、数目字和年月日等。
契丹文是辽代为记录契丹族语言而参照汉字创制的文字,在辽国有官方文字地位。契丹文有大字和小字之分。但从创制到废止,契丹文前后使用时间只有不到300年,主要是在契丹贵族中使用,随着辽国灭亡后便迅速消失成了死文字。可谓“其生也速,其死也速”。
到目前为止,人们所能识别的契丹文字仍屈指可数,但正是这些文字,帮助人们发现了那个远逝了的王朝,和那个销声匿迹的民族的残存踪迹,包括契丹后裔的去向。
契丹是一个古老的北方草原部族。他们自己是也这样讲述起源传说的:在茫茫的北方草原上,流淌着两条河流,一条叫西拉木伦河,意思是“黄水”。人们把它看作是黄河在远方的女儿,所以文献上写作“潢河”。
另一条河叫“老哈河”,也叫“土河”。传说中,一位驾着青牛车从潢河而来的仙女,与一位从土河骑着白马来的勇士,在两河的交汇处相遇,两人相恋,并结为夫妻,他们便是契丹族的始祖。
历史学家根据这个传说和一些相关史料的考证,认为仙女和勇士所代表的,分别是居住在两河流域的两个原始氏族,一个以“白马”为图腾,居住在“马盂山”;一个以“青牛”为图腾,住在“平地松林”。后来两个氏族都迁徙到两河汇聚处的木叶山,他们联姻繁衍,形成了契丹族。
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称汗,国号“契丹”,定都临潢府,也就是今天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的南波罗城。
947年,辽太宗耶律德光率军南下中原,攻灭五代后晋,改国号为“辽”。983年曾复更名“大契丹”,1066年辽道宗耶律洪基恢复国号“辽”。
这以后,“辽”成为这个契丹族政权的固定名称,直到1125年为金国所灭。之后,有辽贵族耶律淳建立北辽,与西夏共同抗金,后被金灭;辽宗室后代耶律留哥与其弟耶律厮不分别建立了东辽与后辽,然后东辽灭后辽,最后东辽也被蒙古所灭。
另外,辽亡后,有宗室耶律大石西迁到中亚楚河流域建立西辽,定都虎思斡耳朵,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楚河州托克马克境内的布拉纳城。西辽政权存在了近百年,于1218年被蒙古所灭。
大辽的最后余响,是1222年西辽贵族在今伊朗建立的小政权后西辽,最后还是被蒙古所灭。
全盛时期疆域曾东到日本海,西至阿尔泰山,北到额尔古纳河、大兴安岭一带,南到河北省南部白沟河的契丹草原帝国,从此永远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里。
而最多时曾拥有120多万人口的契丹民族,也随之消失得无踪无影。
二
然而契丹后裔其实一直是存在的。
史料记载,金灭辽后,许多契丹人被女真人派到北部边疆,修筑抵御蒙古进攻的防御工事“金界濠”,随后就驻防在那里。
金灭后,部分驻防的契丹人在战乱中向北迁移,保持了相对大而完整的族群,这一部分契丹人就是如今达斡尔人的祖先。而云南“本人”源自元代被蒙古人派遣到云南征战的契丹族人的后裔。
辽亡后,一部分契丹人在辽皇室耶律秃花的统领下,归附了成吉思汗。公元1254年,其孙耶律忙古代随忽必烈灭大理,并受命率部留守云南。
《明史·云南土司二》中记载的施甸长官司阿苏鲁,凤溪长官司阿凤即是忙古代的第三代孙,阿苏鲁也被当代“本人”视作祖先。经过740多年的历史沧桑,如今契丹后裔在滇西不下15万人。在繁衍过程中他们和当地民族不断通婚,所以同达斡尔人相比,“本人”同契丹人的亲缘关系要稍远。
研究学者们通过对文字的比较,也发现今天的达斡尔族人和云南境内部分的居民有着与契丹族极为密切的联系。后来又通过DNA的科学实验,更证明了他们与契丹族的遗传关系。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蒋家云家,珍藏着一块《勐板蒋氏家谱》:“蒋氏祖先姓耶律氏,名阿保机,创建辽朝,为金所灭。后裔以阿为姓,又改为莽。在元初,随蒙古军队南征有功,授武略将军之职。明朝洪武年间,因麓川平缅叛有功,分授长官司,并世袭土职。后又经历数代,改为蒋姓。”
保山施甸县木瓜村蒋文良则收藏着《施甸长官司族谱》:“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白马上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驾女来。一世先祖木叶山,八部后代徙潢河;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六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金齿宣抚抚政史,石甸世袭长官司。祖功宗德流芳远,子孙后代世泽长;秋霜春露考恩德,源远流长报宗功。”
这叙述,大体就是契丹族起源传说。
根据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研究所的研究结果,在距契丹先民故土万里之外的云南省施甸县和保山、临沧、大理、德宏、西双版纳等地,发现了15万契丹人的后裔,其中以居住在施甸县的为多。
20世纪80年代末,云南民族研究学者杨毓骧一直对施甸的契丹后裔进行着持续关注。他曾著有《施甸蒲满人(布朗族)社会文化调查》一文。蒲满,是汉文史籍中对云南孟高棉语族诸民族先民的一种称谓,汉、晋时统称为“濮”,清代始见“崩龙”族称,即今天的德昂族,其余仍称“蒲蛮”。
蒲人支系繁多,故素有“百濮”之称。后来,原居于云南南部的部分蒲人,发展为现在的布朗族。“本人”是布朗族内部部分居民的自称。他们认为自己源出北方,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之后。
1992年,来自内蒙古的文史专家,以及包括杨毓骧在内的云南许多专家,一起来到施甸县考察。那次考察的一项重大收获,是在施甸县城东北约6公里处蒋姓契丹遗裔聚居的大竹篷村,也就是长官司村,东山小田坝伯坟坡,意外找了阿莽蒋一世祖阿苏鲁的墓地。
阿苏鲁墓地是一个“轿子坟”,两扇低矮的墓墙,围托着一个并不高大的墓门,斑驳的墓体经岁月侵蚀已老态龙钟,至今没有作完整的修复。其墓碑上书“皇清待赠孝友和平一世祖讳阿苏鲁千秋之墓基”。碑右首行“甲山庚向”四字之下,竟刻有两个典型的契丹小字。
据大楼子蒋氏家谱记载:“有始祖阿苏鲁,任元代万户。及至明代洪武十六年大军克复,金齿各地归附,至十八年二月内,始祖自备马匹赴京进贡,蒙兵部官引奏,钦准始祖阿苏鲁除授施甸长官司正长官职事,领诰命一道,颁赐钤印一颗,到任领事。”
阿苏鲁死于明永乐二年(1404),后因其孙阿龙谋反遭到镇压,阿苏鲁的墓地也被破坏,直到清道光癸卯年(1843)12月4日才为蒋氏子孙重修。
据内蒙古社科院孟志东等专家的考释,阿苏鲁墓碑上的两个契丹小字,译为汉文是“长官”之意。之后,契丹小字研究专家陈乃雄教授也认定,这一发现是完全可靠的,并将施甸县长官司发现的施甸契丹始祖阿苏鲁墓石上的两个契丹小字“穴”读为“太守”或“有司”,正与阿苏鲁曾任长官司正长官的经历相吻合。其后另一位契丹小字研究专家刘凤翥教授在为《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一书所作的序中,也对这些契丹小字予以了充分肯定。
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契丹小字的使用下限是在西辽,而出土的契丹小字碑刻,时间最晚者为金代中期,出土地点则仅限于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北方省区,所以,施甸县发现的阿苏鲁墓碑,则是我国西南部边疆第一次发现的一块刻有契丹字的墓碑,其年代远远突破了历史所载契丹文字使用的下限。
三
13世纪初,蒙古族崛起,相继征服了西夏和金。在金统治下的契丹人,由于复仇心理和对金统治者监防政策的不满,纷纷投向蒙古贵族。投向蒙古人的契丹族人,被编入“探马赤军”中,他们随忽必烈征服大理,并参加了统一全中国的战争。阿苏鲁正是投靠蒙古的契丹后裔,其先祖曾参加西南平叛战争,他是施甸契丹后裔的一世祖。
1253年,忽必烈率大军先后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乌白等蛮三十七部,基本上占领了云南地区。当战争告一段落时,随蒙古军征战各地的契丹族官兵,也大多留居各地从事防戍和屯垦。于是,入滇的契丹族军人,就地安家落籍,开了契丹族入居云南之先河,这就是云南契丹族的来源。
与阿苏鲁墓碑铭文可相印证的是,在云南昌宁县的另一处“本人”墓地里发现的一块石刻,记载着墓主的家世渊源:“原籍乃辽东人氏,后遭逢变迁,保机后裔四散奔走,……移民滇西顺宁而觅其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