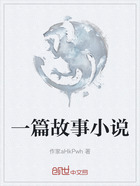
第14章 灶灰试火
御前最近多了几道素斋。
这本是太医院开的方子,说是“去暑养气”。但从灶房到御膳房,再到内务署,这道菜传了三天,宫里人却都知道:皇帝这几日,饭吃得少了,脾气却上来了。
没人敢明说“出了问题”,只听见几个灶下老太监低声说笑:
“哪年换季不是闹肚子?可今年怪的是——闹肚子前,先砍了个值膳的。”
“听说那人是西灶的,出错之前刚从赵奇那边调去,哈,你说巧不巧?”
林郁在一旁烧水,装作没听见。
可这些话,一路从灶房传到配膳,再到内务署,再远一点,就传到皇帝耳边去了。
宫里流传着一句话:“皇上若听见事,不会动嘴;可他眼神一沉,就有脑袋要掉。”
那日午后,内侍宣召,说是小公主赐赏。
林郁低头跪在门外,接过那只香囊时,殿中静得连风都不敢响。
帘后,传来一句淡淡的声音:“你叫林郁?”
“回殿下,是。”
“我记得你,在冷宫那次。”小公主语气如常,“上次没谢你。这东西你收着吧。”
林郁叩首谢恩,香囊温热,藏着一张小小的油纸,上面寥寥七字:
“内监查案,灶房为引。”
他心底悄悄一沉。
——被记住名字的人,不是好运,就是大祸。
三日后,刘副掌印公公带人进灶房查账。
这是个瘦高的男人,皮笑肉不笑,走路拖着绣鞋,像是风吹就倒。但谁都知道,这位刘公公,是赵奇升官路上跌下来的那块台阶。如今赵奇掌印,他却还挂个“副”字,成日盯着谁说错一句话。
“赵公公说了,膳务需整肃。”刘公公进门第一句,便将赵奇推上前头,自己却坐下来喝茶。
他目光扫过一众小太监,最后落在林郁身上。
“你,叫林什么来着?”
“林郁。”
“玉珠哪来的?”他捻了捻手指。
“是小公主赏的。”
“哟,好大的福气。”刘公公笑得轻飘飘,“来人,去翻翻这位有福气的小哥儿箱子——看有没有把皇上的菜谱也写进去。”
很快,从林郁的行李中,翻出一本手抄的食材记录册。纸上字迹密密麻麻,记着天时温度、食材搭配、客人反应,甚至哪天盐重了、糖多了也都有注记。
“你这是想入内膳署吗?”刘公公扬了扬册子,“你要是能活过这一关,本公公替你说句话。”
林郁跪地,语气平稳:“奴才不敢越矩,只是想着,来日若有用,便能多做点事。”
刘公公盯他,笑意更深,“你知道你错在哪儿么?”
“……不知。”
“错在你想得太多,说得太少。”
他转头吩咐,“明日将他送去配库三日,让他学学老实。”
话音落下,灶房静若死水。
那晚,夜风吹动灶口,火苗忽闪忽灭。
林郁独坐灶台边,把那本食材册一页页撕下,送入火中。
最后一页烧着的瞬间,他看见炉灰中还有一片灰烬未冷,角上写着几个烧焦的字迹:
“火中藏骨。”
那是他写的——本打算若真出事时撕下毁灭,谁知有人提前动了手。
外头传来一阵轻脚声,是刘公公的心腹太监,站在门边低声道:
“公公说了,你不是个老实人。”
林郁不语。
“老实人挨打时会喊痛,你从头到尾,连‘为啥’都没问。”
林郁沉默良久,语声微哑:“老实人,都死得早。”
那人轻轻一哼,走远了。
第二日,刘公公突发急症,传说是夜里喝坏了肚子,改口“暂缓配库责罚”。
赵奇未露面,只让人送来一句话:
“让他继续当他的灶下火头。”
灶房里众说纷纭,有人悄声道:
“这赵掌印怕是看中了这小子吧?”
“也许是刘公公撞了枪口,倒了霉。”
“谁说得清呢……如今皇上最讨厌的不就是‘不省心’的么?”
“是啊,听说昨日皇上见了个账本,只说了一句:‘火头上那小子,不错,胆子有分寸。’”
林郁听着这话,没出声,只在夜里添了一把柴,灶火烧得通红,火光里,他的影子贴着墙根,一动不动。
火还不够旺,但已够试一试骨头软不软了。
那夜,他没回住处。
灶火燃得太旺,没人敢来问,他便独自坐了整整一夜,直到灰烬落尽,天色泛白。
他想起那句话:“老实人,挨打时会喊痛。”
可若是太早喊痛,就没人听得见你说话了。
这一回,他赌对了。
小公主的香囊,是遮掩,也是警示。
刘公公的设套,是杀鸡,也是试刀。
赵奇的沉默,是观察,也是默许。
至于皇帝——他未曾现身,却什么都知道。只一句“不错”,就能让旁人三日不敢再动他。
林郁低头看着掌心的水泡,心里却是一片清明。
这世道,最怕的是被记住,又最怕没人知道你是谁。
如今他“被看见”了——不是走运,而是到了能利用自己的第一步台阶。
他起身,把灰扫进簸箕,又将灶台擦了三遍,一丝油渍不留。
他知道,宫里干净不是为了洁净,是为了不给人留下“说你脏”的机会。
等一切做完,他才从衣襟里取出一片干燥的棕叶纸,重新抄写那本被烧掉的食材记。
不过这一次,他不再写全菜谱了,只记材料、温度、分量——没有人能从这上头,再找到“罪名”。
但若有一日,他需要“记得谁吃了什么”,这本册子,也会成为他的刀。
林郁合上册页,抬眼望去,外头日头刚升,灶房却还带着夜里烧过的热气。
他心里一动,忽然觉得有些……高兴。
林郁回屋时,太阳刚好越过宫墙,照在灶房斜顶的青瓦上。
几缕烟还未散尽,空气中有火熏后的焦味。他走得很慢,像是每一步都踩着昨晚没烧干净的余烬。
他刚坐下没多久,门口便来了个小内侍,递了一块冷糕,说是赵掌印打发人赏的,“夜里辛苦了”。
糕是好的,冰镇得透凉,银盘子冷得手都打颤。
林郁接过,低头谢恩,却在那盘子里看见一道浅浅的指痕——是有人用手指蘸过盘面,又抹去了。
那不是传话的手法,那是……“认得你”的痕迹。
他忽然想起昨夜有人在远处站了很久,火光摇曳时照出半张脸,只看得见半截下巴。
不是刘公公那种笑脸藏刀的式样,而是赵奇那种“‘看着你自己出招’的冷眼。”
赵奇没帮他,也没拦他。
但在刘公公中毒之后,配库的命令撤了,查账的名册封了,灶房恢复如常。
有人在传话,说赵掌印护得了人。也有人在笑,说“那是赵掌印钓鱼,不钓则已,钓上来再看是鲤鱼还是死狗”。
林郁听着,面无表情,只是在屋里找出一个破布袋,把那块糕包起来,不吃,也不扔。
他知道,这不是犒赏——
这是赵奇投来的第一颗石子,看水里的人会不会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