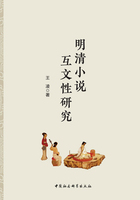
第3章 从叙事学到互文性(代序)
孟昭连
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的实行,学术领域也打破禁区,西方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又一次进入中国。在文学研究领域,“叙事学”的引入,使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小说的研究开了一个新局面。叙事学的本旨是研究“结构”,以发现叙事现象中的各“组件”的功能与相互关系。它涉及一切叙事文体,除了文学还有历史、戏剧、电影甚至新闻传播,而作为叙事文体最典型意义的小说,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叙事学重点研究的对象。1984年,我回南开读研,正值宁宗一、鲁德才二位先生合编的《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台湾香港论著选辑》出版,此书虽名为“古典小说的艺术”,其实所选主要是港台学者用叙事学理论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论文。在后来的三年中,导师鲁德才先生又为我们开设了介绍“叙事观点”的研究生课程。当时的所谓“观点”(viewpoint),是港台地区学者的用法,它不同于以前我们所理解的思想、看法的意思,而是指观察叙述事物的角度或出发点,也有人翻译为“视点”“视角”“角度”,后来比较通行的用法是“视角”。在导师的指导下,我们一面学习这种新理论,一面阅读古典小说原著,用这种新理论寻找问题并加以阐释。几年下来,感觉这种边学边干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的学习方法效果很好,到1987年毕业时,导师和我及师妹马红分工撰写共同完成了二十余万字的书稿《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观点》。虽然因种种原因这部书稿最终没能正式出版,但它记载了我们较早接触运用西方叙事理论进行古代小说研究的历程。稍后由我撰写的关于《红楼梦》的部分内容,改题为《〈红楼梦〉的多重叙事成分》《〈红楼梦〉的人物叙事观点》分别在《文学遗产》和《红楼梦学刊》发表。其后又陆续写过几篇,[1]并且也以《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观点》作为教材,为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过课程。相对于主题思想、人物形象、情节结构等传统的研究方法,叙事学的关注点从“写什么”转移到“怎么写”,或者说从思想论向方法论转化,确实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以至后来对自己的阅读习惯与审美趣味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以前注意的多是人物性格以及反映了什么思想,人物形象注意的是修辞方法、人物语言等。但以叙事学看来,叙述者及叙述的角度更为重要,而以之分析说书体古代白话小说,似乎也更为契合,从中能挖掘出传统研究方法忽略掉的艺术技巧与审美价值。对叙事学的关注,一直持续了我的大半学术生涯。后来随着学术兴趣的转移,研究的重点渐渐转向文学语言这个更狭窄的领域。
从西方引进的任何一个文学理论或研究方法,都有其局限性,不可能涵盖中国文学的方方面面,无法与《文心雕龙》那种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著作相比。叙事学虽然为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者带来了新鲜感,扩展了古代小说的研究领域,但随着叙事学研究对象的无限制扩张,其微观研究的性质渐渐向宏观方向发展,语言文字的属性逐渐模糊了,“叙事”的针对性不是那么强了。[2]有学者认为:“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它已形成了某种套式,缺乏价值判断,影响了研究的深度,并难以与古代小说其他方面的研究协调。”[3]所以古代小说领域的叙事学研究渐呈式微之势。
王凌在读研期间就开始关注叙事学的研究,除了专心上好相关课程,还认真阅读叙事理论原著,搞通原理,并在后来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大胆运用,从语言形式、修辞形式、叙述视角、叙述时间、叙述结构五个层次对古代白话小说文体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描述,不但写出了新意,也为自己后来的白话小说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4]此后,互文性理论也理所当然地受到王凌关注,短短几年就陆续写出了相关论文数十篇,成果显著,俨然是互文性研究的生力军。作为曾经的导师,我自然为她感到高兴。互文性是稍后于叙事学兴起的一种西方文学理论。我们注意到,对于“互文性”这一概念,学术界还存在争议。在中国传统学问中,“互文”本是传统文学手法与训诂学用语。比如在先秦经典中,常有“吾”“我”混用的情况:“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左传·庄公十年》)吾、我意思相同,何以一句话中要混用?胡适曾以西方语法的格数理论加以解释,认为“吾”是主格,“我”是宾格。此说因反证太多,结果沦为语言学研究的笑话。唐代刘知几曾以姚最《梁后略》“得既在我,失亦在予,不及子孙,知复何恨”一语中“我”“予”混用现象为例,认为“夫变‘我’称‘予’,互文成句,求诸人语,理必不然,此由避平头上尾故也”[5]。清人陆以湉以《孟子》为例云:“至《孟子》好辨章,则先言‘予’,继言‘吾’,终言‘我’。盖文家错综变化之法,已肇端于斯。”[6]刘知几的“互文成句”及陆以湉的“文家错综变化之法”,都明确指出“吾”“我”“予”的混用,只是文人的修辞行为,并非口语也是如此。先秦文人对言与文有严格分野,修辞行为发生在书面语领域,[7]互文的运用多是为避免重复,所谓“文家错综之法”即指此。传统互文手法的另一种形式是《辞海》解释的“上下文各有交错省略而又相互补充,交互见义并合而完整达意”。如《礼记·坊记》:“君子约言,小人先言。”汉郑玄注云:“‘约’与‘先’互言耳。君子‘约’则小人多矣;小人‘先’则君子‘后’矣。”诗歌中尤多。大家常举的例子如汉乐府《战城南》中的“战城南、死郭北”、《木兰诗》中的“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唐王昌龄《出塞》中的“秦时明月汉时关”等等,都要前后文合起来理解,表达效果犹如兵家的“分兵合击”。实事求是地说,以上所举中国传统的“互文”与西方的所谓“互文性”并非一码事,其主要差别在于,传统的互文作为一种修辞方式,只是一个遣词造句问题,虽然最终是实现表达的效果,但针对的只是某个字词,与西方“互文性”所指的“一个语篇中出现的融会其他语篇的片段这样的现象”相差甚远。
但这是否可以说“互文性”与中国传统文章手法全无关系呢?当然不是。事实上,站在互文性的角度审视中国传统的文章写法,相似或完全相同的东西俯拾皆是。西方互文性这一概念所指太过宽泛,所谓“文本(语篇)关系”本来就是人类文明积累的基本方式,文字本来就是解决口语瞬间即逝、不能传之久远的缺陷而产生的,如清人陈澧《东塾读书记》所言:“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8]那么任何民族的文字记载无不是在前人基础上进行的,尤其是对于中国古代热衷于“宗经”“征圣”的民族而言,用文字记载的文本之间,必然发生纵向或横向的关系,只是这种关系有巨细之别而已。对此,王凌在本书第一章“古代小说互文性现象的发生依据”有充分的论述,她认为作为一种批评理论和研究方法,既然有可进行比较的东西,能引发我们的联想,更深入地开掘作品内涵,就不妨采取更宽容的态度。比如按照蒂费纳·萨莫瓦约的说法,引用、参考是互文性的基本方式,而在中国的某些文体中,引用前人文本或观点,也是写文章的基本方法。近代刘师培就说:“盖行文之法,固不外征引及判断二端也。”[9]他说的“征引”就是引用前人,而且引得越多越好,越显得有学问。所谓旁征博引不就是说明文本作者要大量引用历史的现实的文献或事实,在此基础上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与结论,文章才更有价值吗?《马氏文通》作者在序言中说:“愚故罔揣固陋,取《四书》、《三传》、《史》、《汉》、韩文为历代文词升降之宗,兼及诸子《语》、《策》为之字栉句比,繁称博引,比而同之,触类而长之,穷古今之简篇,字里行间,涣然冰释,皆有以得其会通,辑为一书,名曰《文通》。”[10]其对前人文献的引用可以说极有代表性。至于文学作品的互文性,王凌举了古代小说《金瓶梅》,可以说非常恰当。号称历史上第一部“文人独创的白话长篇小说”《金瓶梅》,其实它的独创更多表现在立意、全书故事的组织上,而在题材、情节、人物、语言等方面是有所依傍的,它除了在《水浒传》的基础上岔出一枝,重新组织了一个新的故事,而且大量吸收当时流行的话本小说、戏曲、词曲的内容,很多地方几乎是原文照抄。对于《金瓶梅》与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在其刚一问世就被人们发现了。至《红楼梦》出,人们又很快发现它与《金瓶梅》之间的密切关系。脂砚斋在评论《红楼梦》第十三回的情节时写道:“写个个皆到,全无安逸之笔,深得《金瓶》壸奥。”又在第二十八回评点:“此段与《金瓶梅》内西门庆、应伯爵在李桂姐家饮酒一回对看,未知孰家生动活泼?”自20世纪30年代,就有多位研究者探讨过《金瓶梅》与《红楼梦》之间的关系,如阚铎的《红楼梦抉微》就是一部全面对照分析《红楼梦》与《金瓶梅》异同的著作,内容涉及两部小说的各个方面,如“以贾代西门之铁证”“红楼梦以孝作骨,金瓶以不孝作骨”“狮子街与紫石街之不同”“水浒化为金瓶,金瓶化为红楼之痕迹”,等等。[11]事实上,不只是小说,在中国古代文学的不同体裁中,这类与西方互文性理论比较合榫的例子举不胜举。
叙事学、互文性等文学理论的引入,确实为中国文学的批评研究吹进一阵新风,新的研究角度及其带来的阅读感受让人耳目一新。但是也应该注意到,目前这种“新鲜感”还只是局限于研究者自己的小圈子里,对于文学创作者与普通阅读者来说,似乎并无反应。理论上说,文学批评是为阅读与创作服务的,“文学批评的目的及效果有三:文学的鉴赏、文学的普及及改善、公众趣味的教育这三项”[12]。“以透视过去文学,而尤在获得批评原理与文学原理,以指导未来文学。”[13]但事实上,这似乎很难达到,不说读者,就是文学的创作者,真正关心文学批评理论的能有多少?可能并不乐观。总的感觉是,创作、阅读与批评还是两张皮,文学批评的成果沦为“同人”的读物。记得大学时代有汉语语法课,教科书讲到“学习目的”总有“提高运用汉语的能力”“有利于文学创作”的内容。但著名的小说家莫言却说:“实际上,绝大多数的人,一辈子也用不到自己母语的语法,一个基本上不懂语法的人,完全可以正确地使用母语说话和写作。”[14]话说得似乎很“难听”,但作为文学大师级的人物,莫言此说恐怕不是异想天开,而应该是自己的切身体会。那么,文学批评与阅读和创作之间,是否也类似于这种关系?如果不是,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文学研究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与此相关还有一个问题,而且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自20世纪初西风东渐,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全面实现了现代化的转型,基本上实现了与世界“接轨”。但是,也一直存在另一种声音,就是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早在20世纪30年代,老一辈社会学家就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80年代以来,“本土化”的主张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都引起了反响。比如在文学领域,有学者对引进西方理论进行古代文学研究的做法颇有微词,认为并不是所有西方理论都可以成功移植到中国来,因为“西方理论毕竟是从另一种文化传统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西方的理论家在创立一种学说时很少把中国传统放在归纳和思考范围内”[15]。也就是说,完全用产生于西方文学中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可能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甚至会产生南辕北辙的状况。即便像与中国古代小说比较契合的叙事学、互文性,仍然会给人一种用中国千百年前的文学实例,来证明刚刚产生了几十年的西方理论的感觉。这种状况在语言学领域也存在,“几乎一个世纪的群体在本土汉语研究方面选择了西方的知识框架和话语体系。他们忙于翻译、介绍国外语言研究,更有为数众多的学者借着翻译和介绍,直接拿来、直接运用”[16]。不少所谓“研究”就是把西方语法的框子套到汉语的头上,用汉语的实例去证明印欧语言理论的真理性,完全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与知识体系。什么是真正的“本土化”?是继续采取拿来主义,亦步亦趋地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做“填充题”,还是在深厚的文学传统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架构和话语体系,真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也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应该认真反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