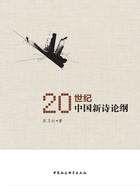
第二节 济世致用的文学观与胡适的尝试
新文化运动开始之时,那些文化精英们拒绝承认传统文学、古典诗歌对新诗有借鉴作用,大多以彻底的、激进的反传统姿态进行文学革命实验,但是作为具有深厚古典文化、诗学传统的一代文人,主观上的拒绝与实际创作上与古典诗歌的血肉联系并不一致,早期的白话诗歌创作表现出某种古今混杂、文白夹生的过渡性特征,这也表明无论多么标新立异的创新,也无法割断与自己的文化母体的血肉联系。
从1918年起,以《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星期评论》《时事新报·学灯》《觉悟》等报刊为阵地,新诗人们开始了用白话写诗的实验,到1919年白话新诗大量出现,创作水平也普遍有所进步,出现了一些比较好的作品。第一批白话诗人主要包括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俞平伯、刘大白、康白情等人,其他新文化主将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都尝试写过白话诗,1922年叶绍钧、刘延陵、朱自清等文学研究会的成员还以“中国新诗社”的名义创办了第一份新诗刊物《诗》月刊,专门发表白话新诗。
胡适(1891—1962)是第一个白话诗人。他之所以倡导用白话写诗,与他希望通过文学革命来改良社会、唤醒民众的启蒙意识有关。像胡适、鲁迅这一代知识分子都受到维新变革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前一辈知识分子的影响,用文学、文化、思想救中国于水火之中,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诉求,当时的文化精英普遍认为,救国须先救人,救人须先救心,启发民智、启蒙民心被认为是当务之急,当历史提供了他写作和发言的机会时,他的文学革命、白话写诗的主张自然会呼应历史的要求,顺应历史的发展潮流。
除了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之外,在美国留学期间胡适在思想上受到美国民主政治、世界主义思潮(国家之上是人类)及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胡适一直被视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把实用主义的思想理念引进中国,希望从思想文化入手,改良中国的世道人心,影响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他对文学持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态度,认为文学应该做到“敏感”与“济用”的统一,当然他更注重文学的“济用”功能。他从“五四”时期开始,直到晚年都坚持实用主义的文学观念,他不太注重文学自身的规律,他认为文学有三个要件,即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以此种标准去指导的创作和批评,自然会排除掉那些给人以朦胧、神秘美感的作品,胡适为文的标准显然是有相当局限的。严格意义上说,他只是借用文学革命来达到改造社会、启蒙民众的目的,是以一个社会学家而不是以一个纯粹的文学家的方式来对待文学的,这种有些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的态度也直接影响了他的文学批评和创作,限制了他的文学才能的充分释放。
胡适在中国新诗的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开山引路之功。他的白话诗集《尝试集》(1920年出版)是中国第一本白话诗集,开启了白话作诗的新时代,其中的一些诗写于他在美国留学时期。胡适1910年考取“庚款留美官费”,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后转入文学院,1915年进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在留学期间就有关白话文学和白话作诗问题与学友们进行过长达一年多的讨论,但支持用白话写小说、散文、戏剧者甚多,支持用白话作诗者寥寥无几,有关文学革命和白话作诗的缘起,胡适在他的自传《胡适四十自述》的“逼上梁山”一节中有详细的记叙。1916年胡适写《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于1917年1月《新青年》杂志上。该文从进化论的角度,表达了“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主张,要求废除文言,提倡白话,使文言合一。他认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这些主张是对前一个时期的文坛复古泥古风气、空洞的形式主义风气的反拨,对新的文学内容和文学形式的呼唤。他的这些对新诗、新文学的主张,明显受到当时在美国文坛非常活跃的意象派诗歌观念的影响。意象派曾把自己的诗歌主张归纳为《意象派宣言》六大信条,有些条款与胡适的“八事”有不谋而合之处(意象派的六大信条包括使用普通语言,但是需用准确的字眼;避免有音无意、用作装饰的诗歌惯用词汇;自由选材;创造新的节奏,表达新的情绪;使用意象呈现出具体、坚定和肯定的画面;暗示出意思,而不是直抒胸臆等内容)。有人甚至认为胡适直接受到庞德1913年发表的《意象主义者的几个“不”》的影响,但通读两者会发现其侧重点完全不一样,庞德强调的是如何去除陈词滥调,准确而生动地去营造意象,胡适则是针对当时中国文坛形式主义的时弊有感而发,批评的是模仿拟古文风,提倡言之有物的自由充实的诗风。1917年7月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要求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他的文学革命主张和白话诗引起社会巨大反响,他是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时期当之无愧的主将。其他作者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以及钱玄同、刘半农的“双簧信”、周作人的《人之文学》都是文学革命开始时期振聋发聩的文章,他们和胡适一起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改天换地的文学革命运动,为中国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胡适留学期间,对英美以及其他外国诗歌的阅读并不广,爱好也不深,可以说是一个业余爱好者,对当时流行的意象主义诗歌虽有所涉猎,但也仅仅是凭兴趣阅读,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新诗、新文学的主张,的确受到美国意象派一定的影响。除意象派之外,英美其他诗歌流派对胡适的影响并不大。他不是一个立志要研究西方诗歌的学者,也无心花大量时间、精力去钻研西方诗歌,但他主张并写作白话诗的确受到英美诗歌的启发,并在1914年就尝试用白话文翻译过苏格兰女诗人林安尼·林萨德夫人的诗《老洛伯》,译诗已经具备白话诗的韵味。而在中国古典诗词方面,白居易浅近平易的诗风和“歌诗合为时而作”的主张,袁枚的诗以及那些朗朗上口的小令、乐府民歌等都对他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他在留学之前也写过不少的文言诗词,对古典诗词的写作套路也有一些探究,但其志趣不在于此。在他发表白话诗之前的所有前期的诗学上的准备为他开辟一个新的诗歌时代奠定了基础。
1917年《新青年》第2卷第6号刊载了胡适《白话诗八首》,这是胡适新诗的最初尝试,虽内容上有新意,但形式上明显受到古典五言、七言诗的影响,其中的《朋友》(后改为《蝴蝶》)的诗是他的第一首白话诗作。胡适的《蝴蝶》用蝴蝶的聚会离散写友情,表达了他在用白话作诗初始知音难求的孤寂心绪,“剩下”的那只蝴蝶虽然孤单寂寞,却不愿飞向天庭,只愿在人间飞舞,这种更贴近地面的飞翔似乎暗示着白话新诗去雅还俗的精神指向,用蝴蝶比喻友谊这在古典诗歌里面是少见的,用白话写出,一、三两句以天、怜为韵,二、四两句以还、单为韵,既有中国古典五言诗的押韵的痕迹,也有西方诗歌押韵规则的影响,虽言新诗,古典诗词的味道还是浓厚的。
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1918年1月第四卷第一号,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三人同时发表九首白话诗,包括胡适的《鸽子》《人力车夫》《一念》《景不徒》,沈伊默的《鸽子》《人力车夫》《月夜》,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题女儿小蕙周岁日造像》,这可以看作是中国新诗的正式登场。此后,在当时的白话杂志刊物上,如《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时事新报·学灯》上,陆续发表白话新诗,一时蔚然成风。
胡适《尝试集》中的诗具有明显的从古文向白话过渡的性质,胡适从“以白话入诗”到用白话写诗的艰难过程,从他的一些诗中有所反映。在以白话入诗的阶段,他还在旧诗词的语法结构支配下加入一些新的词汇和语句,结果写出来的诗半新半旧,文白夹杂,如《鸽子》中的“看他们三三两两/回环来往/夷犹如意”即是如此,他的诗《一念》表达恋人之间的思念之情,是至情之诗,也颇有想象力,诗艺比《蝴蝶》《鸽子》进步。后来胡适意识到必须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才能写出真正的白话诗,他才挣脱束缚,开始大胆尝试。1919年2月他翻译改写的美国意象派诗人拉莎·替斯代尔的诗《关不住了》,让他找到了真正的白话诗的语法及音节的感受,《关不住了》完全没有遵从音律的规则,以非常自由、松散的散文化的方式写出,但原诗的诗味还是得以保留。这首诗被他称作“新诗成立的新纪元”。从这一事例来看,中国新诗的确是在外国诗歌影响下开始蹒跚学步的。当时的学者如朱自清、梁实秋、康白情等人都认为,中国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是外国白话诗输入中国的产物,是对外国诗模仿后的创造。不可否认,中国新诗在很大程度上取法、效仿了外国诗歌,借鉴了其诗歌技巧,创造了自己的新诗。
关不住了
我说:“我把我的心收起,
像人家把门关了,
叫爱情生生的饿死,
也许不再和我为难了。”
但是屋顶上吹来,
一阵阵五月的湿风,
更有那街心琴调,
一阵阵的吹到房中。
一屋里都是太阳光,
这时候爱情有点醉了,
他说:“我是关不住的,
我要把你的心打碎了!”
译自[美]拉莎·替斯代尔(Sara Teasdale)《在屋顶上》(Over the Roofs)
胡适的《希望》(《兰花草》)《湖上》《梦与诗》等作品有些清新可人的诗意或哲理,其他诗作大多诗味不足,太过散文化,正如他在诗《梦与诗》中说的那样,“都是平常经验,/都是平常影象”,“都是平常情感,/都是平常言语”。以这种“平常”的方式所创作的诗自然太过普通、平凡。胡适写诗不够“惊艳”,一方面是因为他缺乏必要的诗才,激情和想象力处中等水平;另一方面是因为一切都在尝试之中,他太注重采用“白话”去写,太强调“作诗如说话”,而不太注重白话写出的“诗”的韵味如何,他显然还没摸索出白话新诗的艺术规律。这首诗的最后几句:“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颇有警句格言的味道。
他写的《鸽子》《老鸦》《权威》等诗有宣扬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的意味,胡适也写过一些反映现实的作品,《人力车夫》《示威》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虽具有文学史的价值,但没多少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
胡适尝试写白话新诗,与其说是因为个人爱好,不如说是出于社会责任,是因为他意识到了白话写诗的可能性和重要性。胡适在新文学开始之初大胆进行多种尝试,开创了一个白话写诗的时代,他的开创之功是其他人无法取代的,虽然从审美的角度审读这些作品,就会发现它们的艺术含量不高,韵味悠长的诗作不多,文献价值大于审美价值,但无论如何,他的白话新诗都可以看作新时代新文学最初的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