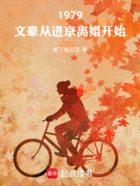
第1章 进京离婚
一九七九年春,燕京火车站。
一辆列车从远处驶来,在此站缓缓停靠。
要下车的乘客,或手提、或肩挑,携带皮箱包袱,牵着半大孩子,一窝蜂涌到车厢门口。
陈阳轻轻一跃,从窗口跳到了站台上。
完美落地。
他拍拍手上的土,拎起行李,看着周围。
“这就是四十年前的燕京火车站吗?”
灰蓝色的中山装汇成海洋,绿色军挎包随处可见,站前广场上竖立着“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红色标语牌。
几个卖烤红薯的老太太缩在棉大衣里,吆喝声被淹没在嘈杂的人声中。
“跟我穿越前那个国际大都市,一点也不一样啊。”
陈阳感慨着变化真大,顺着人流往外走。
出了火车站,直奔公交站。
“信里让我下了火车,先坐10路公交到复兴门,然后……我看看,10路……”
陈阳看着信里写的地址,“嗯,先坐10路,到了复兴门要换乘13路,就到了三里河部委大院了。”
眺望远处,10公交车还没有来,陈阳就在公交车站慢慢等车。
“爷们儿去哪儿啊?等公交车得二三十分钟呢,我这车去前门只要两毛五,走不走?”
一名青年扶着辆自行车,在公交车站从东边挨个问到了陈阳。
“同志,去三里河部委大院多少钱?”
“你?要去部委大院?不是跟我这逗闷子吧?”
青年打量起了陈阳,虽然皮肤黝黑,穿着土气,但眼神里丝毫没有乡下人的畏缩。
尤其五官端正,竟让他产生了一丝丝的嫉妒:“我看你应该是返城的知青吧?”
“不是,我媳妇住那儿。”陈阳摇摇头。
青年羡慕了:“真好,我也想娶个住在部委大院的媳妇儿,这样就不用天天蹬自行车拉活儿了,我他妈腿都遛细了。”
吐槽完,青年算了一下路程,“差不多八公里,上车吧,我只收你两块二就行,保证比你等公交车要快得多。”
“两块二?抢钱呢!”陈阳腹诽。
他从陕北来燕京,兜里一共揣了三十五块钱。
买来时的票花了十五,回去还得花十五,就剩下五块钱的零花。
他还要买高考辅导书,手里自然紧巴巴。
“不用了,我其实挺喜欢坐公交车的,起码不硌屁股。”
“不是,爷们儿,我这二八后座也铺了垫子了,你放心硌不着。”
青年还想再争取一下,但被陈阳坚决的拒绝了,一边嘀咕着‘娶了大院儿的姑娘还这么抠门’,一边骑车往前去了。
“我也不想抠门儿啊,前身娶的那媳妇儿是大院的不假,但人家要跟我离婚啊。”
陈阳叹了口气。
他原本是一名畅销小说作家,短剧兴起后,又去搞了短剧。
结果在一次熬夜写稿时,忽然猝死了。
再醒来,他就来到了1979年,手里捏着一封信。
信里让他来一趟燕京,商量一下李沐清和他离婚的事情。
李沐清是一名女知青,曾在前身的公社插队,一年前在河边洗衣服时,不幸落水,恰巧前身路过,救她上来。
死里逃生之下,李沐清一时感动,选择嫁给前身。
然后就追悔莫及,她这个丈夫初中毕业,见识短浅,除了吃饭睡觉之外,与来自大城市、从小接受良好教育的她,再没有其它话题。
虽然领了证,也住到了一块,但李沐清日子过的很痛苦,坚持同床但不入身,让前身给她一些接受的时间。
前身也答应了。
结果一周过去,燕京政策有变,知青可以返城,李家也给李沐清来信,让她回燕京工作。
李沐清就对前身承诺,先进城带动后进城。
等她说服家人,就来信接前身到燕京生活。
一个月、三个月、半年过去,前身寄了好几份信,可如石沉大海,苦等不到回信。
直到一周前,李沐清寄来了第一封信,内容是要跟他离婚。
前身因为接受不了,脑溢血死了,便宜了陈阳穿越过来,顶替了前身的身份。
“竟然是退婚开局,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对李沐清喊一声‘莫欺少年穷’,嘿……”
陈阳正想着如何应对李沐清以及李家人时。
突然听到有人喊自己。
朝那边看去,一个穿着呢子大衣的年轻男子站在一辆黑色上海牌轿车旁,向他招手。
“这人是……李沐成?李沐清的大哥?”
陈阳回想起李沐清曾给他看过的全家福照片,于是拎着行李走过去:“李哥,你怎么来接我了?什么时候来的?”
“刚来,没多大会儿。”
李沐成打量着这个妹夫,诧异眼前的年轻人,与他妹妹描述的农村青年似乎有些不太一样。
“路上辛苦了。”
李沐成没有多想,接过旅行包放进后备箱,“先上车吧,家里准备了午饭。”
轿车缓缓驶离火车站,长安街上自行车如潮水般流动,偶尔驶过的“大解放”卡车喷着黑烟。
“李哥,李沐清现在怎么样了?”
陈阳随口一问,实则对李沐清的现状并不关心,只是为了找个由头,打探一下李家的想法。
李沐成握方向盘的手紧了紧:“还好,就是工作忙。她在杂志社当编辑,经常加班,
你在下乡可能不知道,现在政策变了,很多人在投稿,
她对这个挺感兴趣的,有时还自己写两篇呢。”
“我知道这事儿,《人民文学》《诗刊》这些杂志都复刊了,连我们小县城都有卖的。”
陈阳侃侃而谈:“最近不是《班主任》《伤痕》特别出名吗,我看杂志上写了好多这种伤痕文学……”
“哦?”
李沐成来了兴趣,“你还懂这些?”
显然是没想到,他妹妹口中的土包子,竟然也知道伤痕文学,还有着独特的见解。
“我老家就是一个知青点,经常和知青一起劳动,所以对这方面了解的多一些。”
陈阳解释:“只不过现在政策变了,除了几个在本地结婚落户的,其余的知青都返城回乡了。”
李沐成瞥了副驾驶的陈阳一眼,知道回避不了,只能主动提起:“陈阳啊,你和沐清的事,你怎么看?”
“李哥,咱们直说吧。当初李沐清嫁给我,是为了报答救命之恩。现在她回城了,想过新生活,我可以理解,也愿意支持。”
李沐成出乎意外的瞥了他一眼。
这个回答太通情达理,完全不像一个被抛弃的丈夫。
“你……不生气?”
“生气有用吗?”
陈阳笑了笑,“强扭的瓜不甜。再说,我和李沐清确实没什么共同语言,不如早早分开,我和她都能开始新的生活。”
李沐成明显松了口气,语气热络起来:“陈阳,你是个明白人。李家不会亏待你的,工作、补偿,都好说。”
轿车驶入一片红砖楼群,这里是部委家属院,门口有军人站岗。
李沐成亮出证件,哨兵敬礼放行。
哨兵看陈阳的眼神带着好奇——一个衣着寒酸的乡下人坐在首长的车里,确实扎眼。
李家在三楼,四室一厅的格局在这个年代堪称豪华。
实木地板擦得锃亮,墙上挂着几幅山水画,茶几上摆着罕见的进口水果。
这居住环境,比他家的窑洞强多了啊。
“陈阳,你来了。”
李沐清走了出来,穿着浅灰色的确良衬衫,黑色长裤,头发剪成了齐耳短发,比记忆中成熟了许多。
陈阳微微一怔。
记忆里的李沐清是个扎着麻花辫的知青,眼前的女人却已经有了知识分子的气质。
李沐清声音冷漠,“路上辛苦了。”
“还好。”陈阳语气疏远,像问候一个普通朋友:“你看起来变了不少。”
“嗯。”
气氛一时有些尴尬。
李沐成适时地插话:“都别站着了,先吃饭吧!妈特意让食堂做了红烧肉。”
饭桌上,李家父母也出现了。
“听说你救了沐清一命?”李父开门见山。
“是,去年夏天她在河边洗衣服不小心落水,我正好路过。”
陈阳简单陈述事实,没有夸大其词。
李父点点头:“救命之恩,没齿难忘。不过……”
他顿了顿,“婚姻大事,不能儿戏。你们年轻人一时冲动,现在想清楚了也好。”
李沐成接过话茬:“我们商量过了,可以给你在京城安排个工作。”
陈阳心中冷笑。
李家这是想用工作来堵他的嘴,免得他到处说李沐清忘恩负义。
可惜他们打错了算盘。
“谢谢好意,不过不用了。我准备参加今年的高考,感觉自己能考上,就不浪费工作名额了。”
饭桌上突然安静了。
李沐清抬头,李父李母交换了个眼神。
李沐成斟酌着措辞:“陈阳,高考恢复才两年,竞争很激烈。你是不是……考虑更实际的选择?”
“比如?”
“比如……我给你在机关找个临时工。”李沐成说,“虽然工资不高,但比种地强。等转正了,还能分房子。”
“谢谢李哥好意,但我还是想试试高考。”
“陈阳!”李沐清蹙起眉头,“我知道你心里有怨气,可这份工作是对你的补偿,你别因为面子,错失了进城的机会,不然,将来一辈子待在山沟里,你一定会后悔的……”
“不是面子问题。”陈阳打断她,“我确实想读书,已经复习一年了。如果考不上,我认。”
这当然是谎话。
穿越才一周,哪来的复习一年?
但他前世作为985高校毕业的作家,因为要写70年代末的小说,查过一些资料,知道79年的高考题不会太难。
以自己的学习能力,好好复习的话,肯定能考一个不错的成绩。
“你……算了。”
李沐清感到失望,她在陈家沟当知青时,就没见过陈阳读书。
还说什么‘我确实想读书’,在她看来,纯粹是为了面子,找的借口罢了。
农村人就是农村人,脸皮薄,眼界低,一辈子难有出息,自己当初怎么脑袋一热,嫁给了这种人?
饭后,李沐成送陈阳去招待所。
一栋灰扑扑的三层小楼,前台坐着个织毛衣的中年妇女。
李沐成亮出工作证,很快办好入住手续。
“明天早上八点我来接你。”李沐成匆匆离去。
房间很小,但很干净。
一张木床,一个写字台,一把椅子,墙角放着洗脸架和搪瓷盆。
陈阳放下行李,坐在床边,长长地舒了口气。
这一天的交锋比他想象的顺利。
李家以为会面对一个哭闹纠缠的乡下汉子,没想到他如此干脆利落。
这反而让李家人,尤其是李沐清,有些措手不及。
“目前,我和李沐清离婚已成定局,明天办理了离婚手续,我就和她没有任何关系了。”
“这样就挺好,我了断了前身的一段孽缘,从此开始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