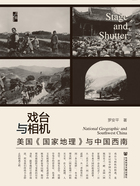
第一节 世界新格局中的“地理知识”
波兰裔英国小说家康拉德的代表作有《黑暗的心》《吉姆爷》《诺斯特罗莫》等。[10]萨义德曾以康拉德为例分析“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认为康拉德是西方对第三世界认识的先驱者,他“既是反帝国主义者,又是帝国主义者”。[11]人类学家詹姆斯·克里福德将马林诺夫斯基与康拉德进行对比研究,认为他们两人都是怀着世界大同理想,在20世纪初奋斗并形成他们自己的“关于一种文化感觉的真与伪”的观点的人,但是,克里福德认为康拉德在这个问题上可能看得更深刻。[12]
康拉德去世前5个月,在《国家地理》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关于地理学和一些探险家》。[13]曾经做过多年海员的康拉德追溯了地理探险家的故事,并以文学化的语言形容不同阶段的地理学:传奇阶段(fabulous geography)、战斗阶段(militant geography)和胜利阶段(triumphant geography)。传奇阶段以哥伦布、麦哲伦的地理大发现为标志;战斗阶段的代表人物是阿贝尔·塔斯曼与詹姆斯·库克[14];胜利阶段是以“未知的南方大陆”和新西兰加入地理的“科学领域”为特征。对于自己在晚年时看到的地理学,康拉德认为那只是“通过学校课程教授的地理知识”,褪去了早期地理探险的浪漫与冒险精神,神秘感消失了,变得枯燥乏味而“毫无生气”。
康拉德一边缅怀已然消逝的激情时代,一边剖析历代探险家的动机与影响。他认为,航海时代早期的探险家们受利益驱使,以贸易之名行掠夺之实,“美洲的发现是历史上已知最为残酷与最为贪婪的时刻”,新世界的发现也标志着富于想象的地理时代的结束。然而对于詹姆斯·库克,康拉德高度认可其地理探险功绩,认为其探险为完全的“科学的探索”。康拉德写道,在后哥伦布时代,“库克的三次远航,可以说毫无污点。他的目的无须掩饰,就是对于科学的追求……作为战斗式地理之父,他的目标只是寻求事实真相。地理学是一门关于事实的科学,而他毕生致力于发现大陆的构造与特征”。[15]
1779年,库克及其船员在第三次探险太平洋期间,与夏威夷群岛岛民发生冲突,库克在冲突中身亡。库克的探险事业是否真如康拉德所盛赞的那样“毫无污点”,当今学界存有争议。人文地理学家菲力克斯·德里弗在其《战斗式地理:探险文化与帝国》中,[16]以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和一些探险家为例,论述地理知识、探险和帝国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一方面,库克的探险对航海科学和世界地理知识的贡献不容否认,另一方面,这类探索引发了西方国家对太平洋地区的殖民,极大地改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并带去了巨大灾难。丹尼尔·鲍在《海权与科学:太平洋探险的动机》一文中,明确反驳了康拉德对库克的评价。他认为除了探险者的个人动机外,还要分析支持其航海的背后力量,库克三次航海的费用皆由英国政府承担,这意味着库克的计划和目的都与帝国殖民行为有关,库克不断把新发现的土地宣告为英国领土,因此丹尼尔·鲍指出,康拉德称库克的航海完全不具掠夺性质,是“不准确的说法”。[17]诸多探讨与反思,在于重新审视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影响及由此构建的世界认知模式。
康拉德对于地理学三个阶段的概括,尤其是对库克时代的追忆,正好映照国家地理学会及其杂志自创办之日起的定位与追求。国家地理学会创建的十九世纪晚期,离第一个地理大发现时代已相去甚远,正处于以库克及其他探险家“填补世界地图空白”为特征的第二个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尾声。《国家地理》编辑马克·詹金斯根据很多历史学家的划分,将第二个地理大发现时代划定为从17世纪末至20世纪初,因此,“在1888年的那个晚上,聚集在宇宙俱乐部炉火旁的人们正处在一个伟大时代的落日余晖中”。[18]这一“伟大时代”,正是西方现代民族国家海外大扩张的黄金时期,其上接欧洲人所谓美洲地理大发现之遗产,下启后轴心时代划分东西、南北的现代世界新秩序。
因此,在这“余晖”中,国家地理学会所推崇与支持的探险事业,与海外殖民扩张息息相关。但是,同康拉德一样,《国家地理》巧妙运用“进步”、“启蒙”与“科学”等话语符号和修辞策略,将英雄探险家的神话一直牢牢地带入并贯穿整个二十世纪,[19]从而一步步为自己树立起“严肃科学、英雄传奇和半官方国家叙事”的形象,由此确立自己的地位。[20]以下,笔者将把国家地理学会及《国家地理》放置于海外殖民扩张和进化论、人类学、博物学以及大众传媒文化等时代语境中进行讨论。
一 海外殖民扩张
1898年4月,美西战争爆发。从海外殖民扩张的背景而言,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成为美国殖民帝国诞生的标志,同时也是美国“国家地理”意识和《国家地理》关注面变化的转折点。经由此战,美国越出美洲大陆而成为一个强大的海外殖民帝国。[21]美国新闻史研究专家迈克尔·埃默里和埃德温·埃默里认为,当时美国的新闻报道对“缅因号”军舰沉没的危机事件采取的报道方式,即鼓吹扩张政策,造成一种战争心态,同美国在整个19世纪推行的对外政策是一致的,扩张主义的确为美国换来了从波多黎各延伸至菲律宾的国土。[22]
然而,作为一个脱离欧洲老牌帝国殖民主义之手仅百余年的新兴共同体,美国国内部分民众对美西战争后国家显现出来的“帝国主义”与“殖民特性”持谨慎态度。艾伦·韦恩斯坦等历史学家指出,“反帝国主义的人害怕吞并行为会损害美国的民主,一部分人是出于道德原因,另一部分人则是出于种族主义原因”。具体而言,道德论者认为,美国不能因为其他社会无力抵抗就对其加以征服,把美国主权强加在独立人民头上的做法是错误的;种族主义者则视管理菲律宾等太平洋上的“野蛮人”为沉重的负担。[23]《国家地理》在美西战争爆发前4个月,曾登载地理学家亨利·甘尼特的《吞并热》一文,明确反对美国的海外扩张,原因之一在于作者认为兼并一个次等级族群,并不利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国家的成长。[24]
尽管反对之声从未停止,但由于对海外市场资源与利益的需求不可阻挡,以及传播基督教信仰的推动,扩张主义的势头最终占据了上风,美国越来越不放过任何可以扩大海外影响的机会,对巴拿马运河的开凿和远东地区的“开放政策”便是其长远战略。其时,国家地理学会董事局成员与杂志的撰稿人中,绝大多数供职于美国政府各个部门,学会基本上是一个半官方组织,因此其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支持便不足为奇。曾担任学会会长34年之久的吉尔伯特·格罗夫纳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美国在世界事务上的兴趣被美西战争所激发,《国家地理》也就从1898年开始转向,致力于持续不断地向大众传播通俗化的地理知识。”[25]
所谓转向,实际上是从以学院式专业地理知识为主转向以通俗的经济地理知识为主,从强调本土地理资源转向更加关注海外地理问题。1898年5月,《国家地理》杂志发行古巴专号,6月及次年2月,连续发行两期菲律宾专号。在此后的十年中,介绍菲律宾、古巴和波多黎各的文章频频出现,[26]关于关岛、萨摩亚等地的文章也不在少数。对远东的中国,这一时期杂志最为关注的是俄国在中国东北修建的跨西伯利亚铁路以及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根据1903年的一篇“地理笔记”提供的数据,美国认识到拥有海外殖民地和享有殖民地利益均沾权的重大意义。1903年,美国对外贸易达到史无前例的新高,来自美国商业劳动部的资料显示,1903年美国进口额突破十亿美元大关,出口额突破14亿美元大关,进出口额在十年内分别增长了18.4%和67.5%,而进口产品主要是用于国内生产建设的原材料。[27]
但是,在商业动机上的直言坦承,并不影响作为新帝国的美国和作为科学机构的国家地理学会被塑造为“进步”、“仁慈”以及“理性”等形象。这借助了《国家地理》所使用的两大修辞,其一为“道德”,其二为“发展”。以对菲律宾的报道为例,朱莉·图森在《〈国家地理〉在菲律宾报道中的帝国意识形态》一文中,认为《国家地理》利用的“经济发展”与“道德监护”双重诉求,即从呼吁美国对菲律宾岛上的自然与人力资源进行直接经济开发利用,到使用更加具有伦理优越感的“道德监护”与表面更为客观的“科学发展”话语,实际上是帝国主义新近发明的一种独特的“美国形式”。[28]
1899年6月,《国家地理》上一篇名为《国家成长与国民性格》的文章,充分印证了朱莉的研究。该文作者为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副会长麦吉,他将美国的“扩张主义”与欧洲的“帝国主义”区别开来,认为新美国与旧欧洲相比,拥有更多自然资源与进取精神,前者无论在哪个方面都较后者“更健康”、“更进步”与“更现代”,进而他反驳那些所谓的“反扩张主义者”:
他们无视人类进步的法则(经由其他科学的准则来衡量人的科学而得出的法则),在这一法则之下,人类沿着井然有序的路径前行,犹如行星轨道一般,经历一些重要的阶段,从野蛮到原始,历经文明开化,最终进入启蒙状态,绝不会倒退,除非遇到灭绝的情况……地球上的族群都毫无例外地要从一个序列进入下一个序列,直至到达最高序列——这一人类法则的要义,我们只能含糊地将其理解为“天定命运”。[29]
从上述话语中,我们可知,《国家地理》对于科学、进步等话语的使用,除了国家利益与国民认同的考虑之外,其背后有着更强大的知识来源作为支撑,这就是20世纪初由生物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等共同强化的社会进化思潮。
二 进化论、人类学与博物学
2004年,《国家地理》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达尔文错了吗?》的文章,开篇即以醒目大字明确回答:“不,进化的证据铺天盖地!”文章写道:“进化是一个漂亮的概念,对于人类福祉、医疗科学以及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在今天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30]科学史作家古尔德认为,达尔文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中获得启发,加上对动植物习性的长期观察,提出了进化理论。[31]其中“物竞天择”这一具有革命意义的思想在生物学领域与社会学领域影响深远,并被不同学科、人群和国家以不同的话语发酵为压倒一切的社会进化论。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热衷宣传达尔文的进化论,其人类进化论的观点甚至成为种族主义的有力武器。海克尔认为:“进化与进步站在一边,排列在科学的光明旗帜下,另一边排列在等级体系的黑旗下,是精神的奴隶,缺少理性,野蛮,迷信和倒退。……进化是在为真理而战中的重炮。”[32]因此,在社会进化论思潮里,“演变”或“选择”内含的多元发生与多样形态,被具有时间方向性的直线进化观所取代,单向度地转化为“进化”与“进步”。正如麦吉所言,人类“进步”的路径如此井然有序,“除非遇到灭绝”,否则绝不会倒退。
人类学家威廉·亚当斯将“进步论”视为人类学的哲学之根,而且是“根中之根”,他认为人类学家所了解的进步论主要是社会进化论。[33]在凯瑟琳·卢茨等人看来,19世纪晚期的人类学,致力于在“低级族群”中寻找进化进程中的“落后”证据,从颅骨测量到婚姻制度研究,以此建立广泛的生物与社会文化目录,都是为了在差别中创造人类社会等级制度。[34]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可以说正成长于这一时代语境中,并且一直不遗余力地向西方世界呈现“原始”图像。《国家地理》在对不同族群进行等级编码时,由于美国其时正处于世界新格局的上升位置,故能运用社会进化论,并以“天赋命运”的盎格鲁-撒克逊式文化优越感,为自己赋予了“进化担保”与“道德监护”的角色,从而为美国在领土扩张后的“国家地理”新书写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帝国的兴起与进化理论的提出是国家地理学会及《国家地理》杂志成功的时代背景,那么,另一个不可忽视的语境就是“科学”概念在学科体制中的变迁。19世纪后期,美国的知识领域大兴实证主义之风,相信世界是可知的,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有秩序与规律可循。这种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使现代学科体制朝向专业化与学院化迈进,经济学、昆虫学、化学、生理学、地质学等学科以及相关机构在1880年代纷纷建立,美国人类学学会(1902)、美国政治科学学会(1903)等相继成立。随着学会呈激增态势且学科门类越分越细,那些掌握多种学问的所谓博学之士成为旧时代的遗老,“业余者”更成为一个轻蔑语。[35]相应地,“博物学”(natural history)这种范畴广阔、兼收并蓄而定义松散的知识领域,地位亦随之下降。
然而就地理学而言,情况却稍有不同。菲利普·保利曾这样写道:“在美国,更为专业的地理研究似乎分布于地质学、人类学、经济学以及工程学里,而地理学会反倒变成与科学没有什么实质联系的探险俱乐部了。”[36]从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成员来看,1888年聚集在宇宙俱乐部的三十三位人士,身份各异,有地理学家、探险家、军官、律师、气象学家、制图师、博物学家、银行家、教育家、生物学家、工程师、测量师、地质学家以及发明家,还有一个记者(俄罗斯问题专家乔治·凯南)。他们大多在联邦政府机构工作,如地质调查局、农业部、民族局等。而被推选为学会第一任会长的加德纳·哈伯特就是律师,是一位富裕的业余科学爱好者与赞助人。哈伯特在就职演说中,强调了自己“业余者”的身份。“我不是一个科学家,我也没有特殊知识可以被称为地理学家。我之所以承蒙大家厚爱被推选为国家地理学会的会长,仅仅是因为我是那些愿意促进地理研究的人中的一员,我与每一位受过教育的人一样对地理研究很感兴趣。”[37]哈伯特在演讲中声明,学会的会员资格不限于专业的地理学家,一切愿意促进地理知识发展的人都可以加入学会。这一原则被写入学会章程:“学会应该根据宽泛而自由的原则组织,只要符合学会利益并以科学为尊者,都可以具有会员资格。”[38]换言之,“学会虽然是一个有限定性的组织,但有钱的业余者不会被排除在外”。[39]
或许正是因为国家地理学会掌门人的特殊身份与兴趣,该学会及《国家地理》杂志在精英与大众之间,发展出一种“通俗地理学”模式。[40]通俗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于其与博物学相通。凯瑟琳·卢茨等人认为,正是《国家地理》“夺回并复兴了走向衰落的博物学,使其经由大众文化得以起死回生”。[41]反过来看,也正是博物学,打造并助推了传媒文化成长期的《国家地理》。在华盛顿广场上,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博物馆,这就是早于国家地理学会20年建立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由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所建。该学会堪称全球最大的博物馆联合体,而国家地理学会的第一任会长哈伯特,也是其董事与重要资助者。如果将国家地理学会比喻为一个巨大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那么《国家地理》每一期本身就是一个展厅,将世界搜集为一个个“封面故事”。
既然与人类学、博物馆有着内在秉性的相似,那么《国家地理》便与人类学、博物馆一样,要面对现代人文学术思潮对文化表述的反思,即洞悉“写文化”(writing culture)、“造历史”(making history)和“权力生产”(creating power)的书写实质。人类学家詹姆斯·克里弗德在《文化的困境:二十世纪的民族志、文学和艺术》一书中认为,搜集和展示是形成认同的关键步骤,而文化描述自身便是一种搜集,是对人群和他们的社会制度与文化实践按照“真实性”原则进行有选择性的搜集。[42]由此,《国家地理》的文化搜集与展示,其“真实性”原则同样需要被讨论。
除了上文提及的美西战争后美国对经济地理与海外扩张的兴趣“被唤醒”,以及大学学院专业学科的增设外,作为一个大众文化机构,在菲利普·保利看来,国家地理学会的发展离不开两个重要条件,其一为大众新闻业的兴起,其二为照相制版术的发展。[43]因此,对《国家地理》杂志表述问题的研究,还应放在传媒文化的语境中去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