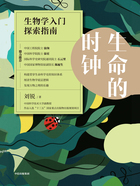
序
探索2000年生物学发展史,建立科学的生命观念
从地球的形成到原始海洋中蛋白质颗粒的出现,再到单细胞原核生物的诞生,生命的起源问题显得神秘又耐人寻味,每一步都像被一双无形的大手精心地操纵着。
生命诞生之后,从寒武纪大爆发到类人猿的直立行走,从进化论的诞生到遗传因子的发现,每一次生物学研究产生突破性成果的过程都显得跌宕起伏……
虽然生物学与我们人类息息相关,与医学、博物学、解剖学、动物学、植物学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在19世纪之前,这一学科一直没有独立的名称。在没有名称的那些漫长的时光里,生物学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演变?
从远古生命起源的观点来看,中国古代有着诸多关于生命诞生的传说,例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古希腊也有类似的传说,天父乌拉诺斯和地母盖亚生了很多儿女,代代繁衍,他们的后裔中有一个叫作普罗米修斯的最为聪明,普罗米修斯用泥土捏成了各种各样的动物,还捏成了世界上第一个人;古埃及的故事与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位叫作库努姆的神用黄泥捏出了人。
大量神话故事被写进了《创世记》,再经过犹太人传递给基督教教徒。在基督教教徒眼里,上帝充当了造物主的角色,对于生命起源给予了绝对的帮助。
当然,也有很多人逐渐对造物主创造万物的观点产生了怀疑,中国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屈原就在《天问》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女娲有体,孰制匠之?”这句话的意思是女娲也是有身体的,那么究竟是谁创造了女娲呢?这句疑问表达了当时古人对于人类起源的思考。
随着时间的流逝,神学思想逐渐统治了整个世界。这一时期,人们对于生命是什么一无所知,对于万物(包括人类)是怎么来的也没有太多清晰的认识,而对动物甚至是人体的解剖是我们获得普通生物学知识的一项重要途径。动物的器官被赋予了更多的象征意义,动物本身也常常被用作部落或者氏族的图腾,因此关于动物解剖的行为对牧师、猎人、祭司等人来说极其重要。原始人类则可以在护理伤口或者进行简单的外科手术时积累解剖知识。
从伟大的医学家、被誉为希波克拉底之后第二位西方医学权威的盖仑开始,人类逐步积累起成熟的解剖学知识。盖仑通过解剖动物类比人体,获得了很多重要的发现。比如,他认为肝脏、心脏、大脑是人体最主要的器官;人的肝脏是五叶的;尿液是在肾脏中形成的,与膀胱无关。但是他也有很多错误的认识,比如,他认为人的腿骨和狗的腿骨一样,都是弯曲的;肝脏的主要功能是造血;血液是呈潮汐式运动的。随后,维萨里、哈维等人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持续的研究。哈维更是通过直接的人体解剖发现了盖仑理论中的200多处错误。
伴随着对各种动植物研究的深入,人类产生了把这些生物进行归类的想法。从甲骨文中就可以看出,中国人在很早以前就形成了朴素的分类思想,他们把植物和动物分成:草、木、虫、鱼、鸟、兽。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动物志》中对500余种动物进行了尝试性的分类,他认为可以根据有无红色的血液,将动物简单地分为有血液的动物和没有血液的动物。当时的博物学家对血液的认知仅仅停留在人和常见家畜的红色血液上。现在我们知道,动物的血液不一定都是红色的,例如,鲎的血液在氧饱和的情况下是蓝色的,虾的血液是青色的。但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这样的分类观点还是远远超出了普通民众的认知。亚里士多德的弟子、植物学家狄奥弗拉斯图(约前371—约前288)提出了另外一种观点:以器官的更新速度来区分动植物。失去器官后,器官更新速度快的是植物,更新速度慢的是动物。
当时的社会还存在一种“伟大的存在之链”的说法,它描述了所有生命形式的层级体系。处在最底层的是岩石和矿物,往上一层是植物,再向上是动物,动物又被分为几个层级,蜗牛和蛇在动物的最下层,最上层是人类,在人类之上的是天使和造物主。这种分类方式代表着当时最朴素的认知。
此外,从遗传学角度看,2 000多年前的《周礼》中记载了谷物的不同品种,《尔雅》中记录了马的不同品种,《本草纲目》中记录了很多有关生物变异的内容,包括金鱼的变异、花卉的变异……从微生物学的角度看,中国有着悠久的酿酒文化,早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包含了“酒”字;在《周礼》中,已经有了关于酒曲制作和酿酒工艺的详细描述。
人类出于生存的需要,首先认识的就是可以充当食物的生物。在古埃及、古巴比伦、中国、古印度等古代文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人们很早就开始从事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植物栽培及动物驯养工作。2002年的《科学》杂志中提到,早在1.5万年前,东亚人就开始驯化狼,也就是今天狗的祖先;在1万年前,生活在南美洲厄瓜多尔的印第安人就开始种植西葫芦和加拉巴木。除了食物,人类还必须面对疾病的挑战,由于认识自然的能力及与自然抗争的能力相对较差,除了利用动植物进行治疗,传统的医学也开始萌芽,动物体乃至人体解剖的活动让人类能够充分认识到人体的构造……16世纪,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兴起,以研究植物、动物、矿产为主要内容的博物学在欧洲逐步发展,人类由此进行了对生物本质的探索,对生物进行了简单的描述和记载。
17—19世纪,伴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发展,生物学取得了长足进步。詹森兄弟、列文虎克、罗伯特·胡克、马尔比基和尼希米·格鲁等人发明了显微镜并改进了显微镜的显示倍数,观察细胞和各种生物成了古典生物学的热门研究领域。1735年,瑞典生物学家林奈出版了《自然系统》,创立了生物分类的等级和双名法,让生物研究有了明确的归类范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生物命名法的确定让原先混乱的生物按照某种特定的分类标准形成了各自独特的体系,对于同一物种的研究不会再出现各自为政的情况,研究信息更加透明,研究步伐得以加快。1839年,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和德国动物学家施旺共同创立了细胞学说,成为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1859年,《物种起源》的出版动摇了上帝创世和物种不变的唯心主义观点。
19世纪初,“生物学”这样一个新兴又包罗万象的词诞生了,细胞生物学、遗传学、免疫学、微生物学、生理学、胚胎学、分子生物学等分支学科纷纷建立。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蓬勃发展,人们在这些学科与生命科学之间进行了广泛的交叉研究。1866年,奥地利神父孟德尔发表了《植物杂交实验》一文,奠定了现代遗传学研究的基础。随后,美国生物学家、“现代遗传学之父”托马斯·摩尔根在此基础上以果蝇为模式生物进行研究,继续提出遗传学的连锁和互换定律,用实验的方式将遗传规律清晰地呈现在公众面前。至此,遗传学的三大基石呼之欲出。
19世纪,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证明了微生物不能在短时间内“自然发生”,通过实验证实微生物必须经外界环境引入;苏联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在心脏生理、消化生理、高级神经活动生理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构建了条件反射理论;德国博物学家海克尔、德国生物学家施佩曼在动物胚胎发育研究方面取得重要发现,通过实验胚胎学证实了被移植的组织和宿主都可能参与二级胚胎的形成;1944年,美国细菌学家奥斯瓦尔德·埃弗里通过肺炎双球菌转化实验证明DNA(脱氧核糖核酸)是遗传物质。这一系列研究都证明了实验设计的重要性,生物学家已经不再简单地局限于观察生物、描述生物,而是在用实验论证自己的观点。
1953年,美国生物学家沃森和英国生物物理学家克里克提出了DNA双螺旋结构模型,以这一事件为分水岭,人类步入了分子生物学时代。生命科学的研究逐步向生命的本质深入,分子角度的研究领域成为热门。1957年,克里克提出了遗传的中心法则,指出生命信息的流向;1961年,法国分子生物学家J.莫诺和F.雅各布提出了乳糖操纵子模型,开始尝试探讨基因调控的原理;1966年,美国生物化学家马歇尔·尼伦伯格破译了64个遗传密码,成功解析将所有生物的遗传信息解读成蛋白质的规律;1975年,德国免疫学家科勒和阿根廷免疫学家米尔斯坦研究获得了淋巴细胞杂交瘤,进而发明了单克隆抗体技术,开启了临床诊治领域研究的先河;1990年,美国政府启动了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在1999年加入其中,并且承担了3号染色体短臂的测序任务;2005年,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测序工作全部完成,这项工作的完成是全世界多个国家的科研中心通力合作的结果,人类这本由30亿个碱基对组成的天书完美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探究生命的本质,并且开始有目的地研究和改造生物,成为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
在从事科研工作的过程中,我深刻地感受到科技的重要性,科技强则国强,科技兴则国兴!这一切都依赖于国民整体科学素养的提升。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开始接触科普,想写点儿关于生命科学普及的内容。在当今社会,信息量骤增,五花八门的内容将我们团团包围,人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辨明真伪,很多人还缺乏基本的科学常识和科学精神,因此科普工作刻不容缓。
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深知应该在研究之余尽微薄之力,让科学精神、科学素养惠及更多人。因此,我想用最朴实的语言,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帮助大家构建对于生命最朴素的认知。
2021年6月,国务院印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简称《科学素质纲要》)。《科学素质纲要》指出2025年的目标是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15%。这对我们的工作来说,既是促进,也是莫大的支持与鼓励。
知识是无法穷尽的,我们应该尽己所能地多了解一些。终此一生,也许我们无法成为科学界的巨匠,但是我们可以在科学发展的历程中做一个安静的观察者和倾听者,让科学精神和理性思维的种子在我们的思想中萌芽、开花、结果。
接下来,让我们开启生命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