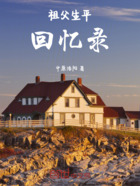
第2章 汉城旧事
沿着滚滚的汉江之滨,一座名为汉中的古老城市坐落于此。汉中,是高祖刘邦的起兵地,是汉文化的萌芽地,是汉帝国的前身,也是汉民族的正源。
千年来,汉中这个在泛黄史书中出现过无数遍的名字,一次次给世界留下深刻的印记。
遥望西周末年,倾国倾城、致使幽王甘愿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就出生于汉中南郑一带。
秦末农民揭竿而起,旧贵族纷纷复辟。刘邦则被项羽封为汉中王,至今在汉中仍留有韩信拜将坛、褒河栈道、古汉台等历史遗迹。
等到楚汉争雄落下帷幕,运筹帷幄的谋士张良被封为留侯,正是在汉中留坝。两汉帝国繁荣昌盛,出使西域的博望侯张骞、发明造纸术的蔡伦,都分别出生于汉中城固与洋县。
东汉末年分三国,汉中更是天下豪杰的必争之地。先有张鲁虎踞汉中,后有刘备称汉中王,继而黄忠于汉中定军山下刀劈夏侯渊,又有张飞获封候于汉中西乡。而最令人遗憾的,便是武侯之死。诸葛丞相也随着棺椁葬在了汉中勉县。
近代以来,汉中亦是红色革命的发祥地之一。以陈潜伦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组织成立了红二十九军,在川陕一带进行着早期革命。
可以说,汉中的故事就是汉人的故事。汉中不仅拥有浓墨重彩的人文气息,更拥有着沉甸甸的历史底蕴。
而我的祖父,就出生于汉中。准确来说,是出生于1942年的HZ市城固县博望镇徐家园村,毗邻张骞墓、贯穿于平坦无际的田野。
我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不信鬼神,更不信玄学之说。但自小生活在博望侯坟边的人们,也许真的有一些天命——或是耳濡目染。
1942到1949年间,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并都取得了胜利。然而那时祖父的年龄很小,对社会变革的记忆并不清楚,因此我无法通过祖父的口述来还原那段历史。但我相信,在1945年与1949年两个节点上,汉中当地也一定是欢腾一片。
祖父十四岁那年,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曾祖父不幸去世。祖父说,当时他的父亲是患上了风寒,但由于医疗条件不发达,致使病情愈发严重。咳喘、发热以至于惊厥。我猜想,这种病症可能源于某种早期的流感病毒。
旧时代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的生活环境也十分艰苦。当我听到这个故事时,我常常会设想,倘若当时有一粒抗生素,那么后面几十年的一切是不是都会朝着另一个轨迹发展?
祖父那时年纪尚小,却正值青春意气之时。曾祖父去世后,祖父曾将请来的郎中推下田坎,因为在他的心里是不愿意接受父亲的死的。他认为,一定是郎中的医术出了问题。
由此一段简短的记忆,不难看出祖父年轻时是一个率真且有脾性的青年。这种性格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都伴随着祖父,有时为他带来了幸运,有时也不免成为了一些阻碍。
祖父的父亲过世后,一家的重担便落在了他的母亲身上。我的曾祖母,虽然我素未谋面也很少听闻,但我始终对她抱有暗暗的敬意。这个平凡的农村女人,将祖父以及三个兄弟、两个姐妹拉扯成人。其中也不乏很有出息的后辈。
什么是独立、自由、强大的女性?我想,大概就是几十年前的那种红色标语:“妇女能顶半边天”,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大劳动人民的生身母亲。
祖父是一家中的老三,上面有一位姐姐和哥哥。曾祖父去世后,祖父的姐姐和哥哥便早早担起了抚养家庭的重任,而祖父则在当地旧时的学堂校园里求学。文化,是改变他们命运的关键钥匙。
十年寒窗终得报,百里喜传久欢笑。
在那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年代里,祖父一家啃过草根树皮、吃过观音土,唯独没有放弃过学习文化知识。
祖父非常喜欢读书,在没有网络和各式各样的娱乐产品的年代,书籍是孩子们获取知识与快乐的难得途径。
祖父说,自己常在放学途中手捧小人书、连环画。诸如秦琼卖马、三国演义、西游水浒……这些都是祖父反复阅读揣摩过的经典名作。
那时还很少有高中、大学,初中毕业后成绩最好的人会优先选择上中专。而祖父凭借手不释卷的功夫,终于考入了当时当地的名校:城固师范。
按祖父的年龄推算,读师范时大约是1957年到1962年之间。彼时的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又处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更迭的关键时期,普通农民连衣食饭饱都面临着巨大的威胁。
据我所知,几十年前读书考上学后,多数人都会选择商、医、师等职业。也正是这一批前辈们,哺育了中国腾飞的四十年的中坚力量。
祖父选择去师范读书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师范学生管吃管住且减免学费,毕业之后还会分配工作。这对于当时压力极大的家庭来说,无疑是最好的抉择。
据祖父口述,他的数学很不错。我和堂姐幼儿园及小学时的数学,祖父也时常给予我们教导。
由于祖父的父亲逝世很早,家中又有六个孩子需要开销,所以祖父一家的生活十分贫苦。很多时候,连一碗热腾腾的饭菜都是奢求。
祖父读师范时,学校会定期分发一些一些粮油和面馍,祖父从来不吃这些难得“美味”,而是把它们攒起来,到周末时带回家给弟弟妹妹们改善生活。
十七八岁的年纪,却扛起了大梁。这份回忆在祖父看来,既苦,又意义非凡。每一段艰辛,都会使人成长与强大。无不从里里外外塑造着一个人的个性与品质。
几十年前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电影里常演绎得十分动人,而现实总是不会那么甜蜜,兴许会有些遗憾和含蓄。
祖父身高175厘米。听祖母说,他二十多岁时还长了个儿。那时候,这个身高已然鹤立鸡群。加之英俊端正的外貌,祖父在师范学校里备受青睐与关注。
祖母曾笑道,祖父上师范时,有许多女同学把自己的布匹、粮食送给祖父。在那个慢节奏、含蓄、困难的年代,这些行为显然是对祖父的示好与追求。祖父则打趣道,自己年龄小什么也不懂,只当是人家一片好心而已,现在想起觉得甚是可惜。
女同学们会凑钱、凑票,给贫寒的祖父买生活用品,锅碗瓢盆、小说图书。前些日祖父谈起时,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这段经历让我想起来那句“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对比现今花花绿绿、灯红酒醉的快节奏社会,我不禁对祖父的少年经历有了种隐隐的向往。
祖父和祖母的相识很平淡,也极具时代色彩。祖父在读完师范后被分配到了西乡县的两河口工作,十九岁的他英俊高大又兼书生气质,于是十里八乡最出名的媒人便前来为爷爷的婚事牵线。
祖父去往西乡,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而这些事情我会在今后一一讲到。接下来的记述,我将从我的祖母展开。
祖母也是城固博望人,生于1944年的张村,姓王,家里是一对姐弟。祖母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但也读过一些书,年轻时曾在人民公社做过记工分、打算盘理账等工作。
即便来源于媒人的引见,也不妨碍祖父对祖母的一见钟情。很快,这门婚事就被敲定了下来。
往后六十余年里,祖父对祖母的爱和关心从来分毫未减。在伯伯们与父亲的记忆中,祖父和祖母从未有过争吵。而在所有人的印象中,祖父都非常爱祖母,对她呵护有加、耐心至极。
直到不久前祖父病倒,医生通知他住院,祖父仍执拗不肯。不住院是祖父的顽固,也是他对祖母的深深的爱。祖父怕祖母一个人晚上在家睡觉会害怕,也担心祖母在医院会染上流感。还有更多的事情,我会在后面的书中陆续谈及。
很难想象,一段跨越六十多年的爱情,一段媒人牵线而成的婚姻,居然能够在如今这个时代中令人赞叹、感慨不已。
没有人知道祖父为何如此爱祖母,更没有人懂得该如何维护一段六十余年的爱情。在科技发达的二十一世纪,似乎六年的爱情都寥寥无几、弥足珍贵。
在大家的记忆中,祖父与祖母和谐一生、如胶似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婚姻从未有过任何裂痕或渣滓。这既源于祖父的责任和爱,也源于祖母的贤惠温柔。
不知听谁提过,似乎祖母曾与祖父的母亲、我的曾祖母关系不是很好。往事如烟如尘,其中细节早已无法追究。但我想,可能是因为曾祖母是一个刚烈要强的女人,毕竟她独自将一众孩子拉扯成人,而祖母则是个内敛少言的女人,所以导致了她们的性格不合。
但总之,祖父祖母的婚姻与爱情,足以让我们每个人都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祖父从城固师范毕业后,本可以成为一位人民教师。但由于时代因素,最终被分配到了西乡县两河口镇做文书。没有成为教师,也许是少年志向的遗憾,但从后来的经历而看,这其实是很幸运的结果。
西乡县,是我的家乡,是我出生的地方。与城固县交界,隶属牧马河水域。相较于城固的一马平川,西乡除了县城外便多是深山老林。
西乡县西南与四川交界,几个大镇同巴山山脉一道沟壑纵横。而祖父所工作的两河口镇,更是西乡县最偏远的镇之一。在那个交通极不发达的年代,距离的阻碍也被无限放大。
据祖父说,步行是最常用的交通方式。
打开高德地图,从现代发达的公路步行,城固博望到西乡两河口的距离是138公里。而祖父曾无数次带着几日几夜的干粮徒步穿越大山走过这段路程。
两河口镇,坐落于西乡的东南方向。与镇巴县接壤,属于巴山山脉。几十年前的两河口镇人烟稀少、鸟兽众多,去往那里除了要克服交通的阻碍,还需当心随时出现的狗熊野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