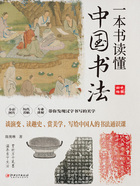
第三节 东汉草书集大成者:张芝
东汉时期,草书发展迅速,人们更重视笔画的流畅和律动,更重视相邻字之间气韵的传递和衔接。这一时期出现了书法史上的第一位草书大家,也是东汉草书的集大成者——张芝。
张芝(?—约192),字伯英,敦煌郡渊泉县(今甘肃瓜州东)人。相传,张芝自幼喜欢书法,刻苦练习,篆书、隶书、章草都很擅长,最终他集众家之长,开拓创新,在章草的基础上创立了今草。
张芝学书极为刻苦,西晋卫恒《四体书势》中记载:张芝“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后人称书法为“临池”即来源于此。怀素在《自叙帖》中说:“夫草稿之作,起于汉代,杜度、崔瑗始以妙闻,迨乎伯英,尤擅其美。”张怀瓘《书断》中说:“伯英学崔、杜之法,温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脉通于隔行。……伯英,即草书之祖也。”今草书体中保留草篆的圆实而活泼的线条特点和草隶飘逸的体势特点,同时大幅度增加了章草中已经出现的运笔连绵和结构简略的特点。
宋代《淳化阁帖》收张芝五帖,除《秋凉平善帖》为章草外,其余《冠军帖》《终年帖》《今欲归帖》《二月八日帖》四帖均为今草。其中,《冠军帖》又称《知汝帖》,是张芝的今草代表作。此作一气呵成,气脉通连,隔行不断,是“一笔书”的早期经典。作品发挥得淋漓尽致,精神照人,同时又险象丛生,而具险笔之处,往往又在险中扣稳,使诸字之间有静有动,在更高层面上达到均衡。这些作品的意义,在于用笔、结体、布局全用今草规范,章草横势字势和运笔特点荡然无存,使观者的审美感受也完全不同于章草时代。
对张芝此作,后世多有学者发生质疑。如清代王澍《跋临伯英章草》中说:“《淳化》所载伯英狂草,皆俗手伪书。惟《秋凉》一帖,笔法淳古,为伯英手耳。余以右军《豹奴帖》笔意临之,亦略同其趣。”
张芝《秋凉平善帖》又称《八月帖》。为章草,八十字。其迹高古可爱,冠绝古今。该帖章草少有夸张形式的“燕尾”,收笔含蓄,大多作点或捺点,或者回钩下连,具有今草气息。
此帖仍是字字独立、无字间连带,但单字之间已极显大小错落,字内连带增加,字间气息极显连贯。更重要的是,多数单字的用笔和结体已处于章草与今草之间,特别是帖尾“幸甚幸甚”用了省字符号,这在皇象等较早章草书法家笔下也是未曾得见的。
张芝的草书成就,向后世呈现出汉末今草已经成熟,章草与今草并存的一种书法文化形态。深刻把握张芝兼善章草与今草的实情,也有助于解决书论史上多年未得确解的疑题。
卫恒《四体书势》中说:“(张芝)下笔必为楷则,常曰‘匆匆不暇草书’,寸纸不见遗,至今世尤宝其书,韦仲将谓之‘草圣’。”后世学者每为“匆匆不暇草书”聚讼纷纭。其实如将这里所称的“草书”理解为字字独立、犹带隶书遗意的章草,而非运笔疾速、重视连写的今草,也就不难理解——与今草相比,章草确实是难以“匆匆”写就的。张芝在当时得享“草圣”之名,也是依靠其章草成就,宋代姜夔《续书谱》中说:“大凡学草书,先当取法张芝、皇象、索靖章草等,则结体平正,下笔有源。”由此亦可见张芝章草成就之高。传为张芝所书的《秋凉平善帖》,字形灵活多变,大小不拘,其法古雅,风格独具,帖中有些字已和今草相似,有萦带使转的特点。
今草最大的特点在于字与字之间不再是独立的,而是可以连笔书写。这在今天看来已经习以为常,在当初却极具开创性,因为此前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一旦突破了字与字之间的这层关系,书法的艺术性便陡然大增,以至于后来出现的狂草也是完全建立在连笔的基础上。此外,今草与章草相比较,隶书的痕迹已经基本完全消失,更讲究行笔的流畅和所传达的气韵,将笔画中蕴含的律动感更充分地表现出来。张怀瓘在《书断》中如此评述张芝的今草:“如流水速,拔茅连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奇形离合,数意兼包,若悬猿饮涧之象,钩锁连环之状,神化自若,变态不穷。”
由于张芝等章草、今草书家的影响,东汉末年出现了书法史上空前的草书“书法热”。东汉末年赵壹的《非草书》对当时社会酷爱草书的种种有穷形尽相的描写。
赵壹(122—196),本名赵懿,字元叔,汉阳郡西县(今甘肃天水市西南)人。辞赋家、书论家。《非草书》一文是现存最早的单篇书论,该文反映出当时社会上文人竞习草书如火如荼的态势。作者立意虽在表示对这种风气的否定,但所述内容向后人展示了草书在当时文人士族中之火爆程度。文章开篇说:“余郡士有梁孔达、姜孟颖者,皆当世之彦哲也。然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孔、颜焉。孔达写书以示孟颖,皆口诵其文,手楷其篇,无怠倦焉。于是后学之徒竞慕二贤,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为秘玩。”可见当时文人士子追慕张芝草书竟远超过儒家道术。当时人苦练草书的情状则是:“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䚡出血,犹不休辍。”众人迷恋草书到了不知疲劳、不省晨昏,甚至伤及身体健康的痴狂程度,成为书法史上一出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