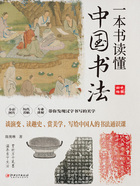
第二节 商、西周金文
商代金文的产生
金文的载体主要是青铜器,金文就是铸或刻在青铜器具上的文字。古人习惯把铜称为“金”,所以这些青铜器上的文字被后世学者称作“金文”。
中国古代对铜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六千年前,传说夏禹曾经铸造九尊大鼎,但没有流传下来,上面是否刻有文字也不得而知。随着古代科技的进步,商代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已经十分成熟。商代之后的两周青铜器留存较多,人们对金文的认识便得益于这些青铜器。
青铜器是天子、诸侯及王公贵族所使用的珍贵器物。许多青铜器是因诸侯或王公贵族受到天子的赏赐而制作,工匠往往受命在上面铸刻说明其铸造原因、所属主人族名或国家大事的文字,这便是金文大致所记的内容。又因带有金文文字较多的青铜器主要是编钟和鼎两类,所以金文又被称为“钟鼎文”。金文从式样上看主要分为两类,线条凹进的称为“款”,线条凸出的称为“识”,同时青铜器又别称为“彝器”,所以金文还有个别名,叫作“彝器款识”。
早期的青铜器上铭文字数较少,通常不会多于十个字,有的仅有一两个字。随后,青铜器上的铭文字数渐渐增多,到周代中后期,青铜器上铭文字数上百者已不少见。
从字体的演变来看,金文的前身无疑是甲骨文,许多金文的结体保留着甲骨文的形态特点,象形意味浓重。只是由于书写技术和载体的不同,金文与甲骨文相比,更具有自身明显的特点。
甲骨文是用刀一次性刻出来的,所以文字直线多,线条细。金文极少直接在青铜器上凿刻,往往是在做泥坯的时候刻在泥模上。泥坯比甲骨要软得多,刻出来的字往往粗壮、圆浑,在笔画交接处还会出现粗点。金文的整体风格是粗粝中带有质朴、厚重之感。
金文在笔画更加粗浑的同时,还大量使用曲笔,因而影响到字体和笔画。一是字体变圆,甲骨文字体有些随意,金文则是明显经过组织和考量,整幅铭文的文字结构比较统一,或是上方下圆,或是内方外圆,十分和谐;二是笔画变圆,尤其是在笔画的转折处,大量使用曲笔,显得雍容大度。
在结构布局方面,甲骨文的布局受制于材料,同一块甲骨的不同部位,会存在纹路不一和软硬不同的情况,锲刻出来的字形往往参差错落,时疏时密。在早期的青铜器上,金文字数很少,布局尚遗留甲骨文书法的特点,缺乏整齐的要求。随着金文的成熟,文字篇幅越来越大,铭文逐渐讲究布局。与甲骨文尚无统一的排布规则,出现过很多种几何形状的排列方式不同,金文讲究统一的竖行排列。长篇金文往往会布局成长方形,一列列文字排列整齐,看上去紧凑、大气。
甲骨文存在的目的多为记载事件和卜辞,金文除记载大事之外,还具有装饰的功能。青铜器制作费时,非常珍贵,从整体样式到纹饰,再到上面铸刻的铭文,都要求美观,具有观赏性。金文的整体布局更为规范、整齐,与青铜器本身的造型相和谐、统一,在表意的同时,又起到装饰效果。
甲骨文最初被发现时已让人十分惊叹,作为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成熟文字,甲骨文一出现就已是比较成熟的文字了。而金文的出现同样如此,从后世出土的青铜器看,金文在商代很快即达到极高的艺术水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当时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发展迅速,文字凿刻也日趋成熟;二是青铜器作为国之重器,统治者格外重视,派由技术精湛的工人从事此事,从前期设计到后期成形,皆要求精致。
商代的金文以成熟的文字形态出现,可谓横空出世。但金文真正的成熟期是在随后的周代,后世所公认的大批金文经典便诞生于周代。
西周金文的成熟与鼎盛
周代是青铜器和金文发展的巅峰时期。周代历史有近八百年,金文不仅作为文字得到了长足发展,其作为一种艺术也发展得更为成熟。
文字和书法反映一个时代的主流审美。周人已基本上抛弃了商代尚武和强悍风格的审美趋向,更注重文字本质特性的回归。反映在金文中,其明显减少了粗糙和杀气,增添了朴实和浑圆的特点,比如方折笔画已几乎不见,而代之以圆转笔画,文字布局更加规范、和谐。
到西周中期,金文进入成熟阶段,每个字的书写都有了固定的结体。这段时期金文主要有如下特点:一是大量使用圆笔,笔画弯曲处显出圆润的味道,这一特点也影响到后世隶书、楷书、草书中笔锋的转换;二是字体变得更加均衡、稳重,这要得益于字体中横竖变得更统一;三是布局更有章法,主要呈现为竖成列,字与字的间距较小,列与列的间距略大,使通篇文字不至于拥挤,显得整齐又大气。

大盂鼎全形拓
周代的金文代表作很多,如大盂鼎、毛公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的铭文等。
大盂鼎,西周康王时期铸造,清代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京当乡礼村(一作眉县礼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有铭文19行,291字。大盂鼎铭文布局完整,字体匀称严谨,能够看出作者是在有意识地追求统一和谐的效果,这与之前的甲骨文审美有着明显不同。书法用笔含蓄内敛,没有过分夸张的地方,线条苍劲有力,饱满浑厚,更显质朴和大气。作为西周初期的作品,大盂鼎铭文已经体现出相当高的书法艺术水准,其中体现出的朴厚、圆润、中和之美,不仅是当时王朝强盛的体现,更为日后中国书法的发展和审美确定了方向。
散氏盘
散氏盘,也称为“散盘”“夨人盘”,清代出土于陕西凤翔,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周代散国位于陕西宝鸡凤翔一带,西北方与夨国为邻。青铜器断代上一般将散氏盘定为周厉王时期器物。散氏盘铭文19行、350字。内容为土地转让,记述夨人付给散氏田地之事,并详记田地的四至及封界,最后记载举行盟誓的经过。除书法的研究价值之外,它还是研究当时土地制度的重要文献。散氏盘与毛公鼎、虢季子白盘、大盂鼎并称为“晚清四大国宝”。
散氏盘铭文在周代金文作品中可谓另类,它既具有同时代青铜器铭文质朴、大气的特点,又在笔法、字体结构和布局上凸显出鲜明特点。在用笔上,这篇铭文不像其他作品那样追求端庄、秀丽,而是呈现粗犷、豪放的特点,但又能粗而不俗、古朴自然。在字体上,散氏盘铭文中的金文比其他西周金文形体要略扁,字态以横向为主,这一特点后来被隶书汲取。在布局上,这篇铭文没有墨守成规,而是大胆地创新,很多字形都是偏的。但是从整体效果上看偏中有正,形散神不散,表面笨拙,实则巧妙,表现出散漫肆意的豪放之气。散氏盘铭文书法在周代金文已相当成熟的时期,呈现出一种返璞归真的艺术气象,具有较高的美学和艺术价值,被后世历代书法家所推崇。

散氏盘全形拓及其铭文拓片
毛公鼎
毛公鼎,为周宣王时期铸造,清代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毛公鼎高53.8厘米,口径47厘米,共有铭文32行,除去失铸的两字与“卅”的合文有497字,是所有出土青铜器中铭文字数最多的一件。据铭文记载,西周宣王初期,大臣毛公 振兴朝政,辅佐周王,最终使王朝出现中兴气象,宣王赏赐毛公
振兴朝政,辅佐周王,最终使王朝出现中兴气象,宣王赏赐毛公 以重金和车马等物,毛公
以重金和车马等物,毛公 将这件事铸在鼎上,以示纪念,这也是毛公鼎名字的来历。
将这件事铸在鼎上,以示纪念,这也是毛公鼎名字的来历。
毛公鼎铭文是西周后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笔法严谨、凝练,起笔多用圆笔,收笔时则多用尖笔,刚柔并济,章法有度。字的结构,圆中有方,方中有圆,转换自如,融会贯通。布局上,整篇铭文环鼎铸造,洋洋洒洒,气势壮观。无论从整体布局,还是从每个字的处理上,毛公鼎铭文都能让人感受到制作者的严谨和用心,达到笔意、文意相通的境界,这在当时非常难得。历代文人和书法家对毛公鼎铭文皆赞赏有加,晚清李瑞清在此鼎题跋中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对毛公鼎铭文有这样的评价:“此铭全体气势颇为宏大,泱泱然存宗周宗主之风烈,此于宣王之时代为宜。”

毛公鼎铭文拓片
虢季子白盘
同样属于周宣王时期的名器,虢季子白盘的铭文则是另一种风格。此盘是虢季子白受周宣王赏赐之后铸造的,以作纪念。这篇铭文的字体修长瘦美,方笔和圆笔的运用切换自然,字形中间收紧,上下左右则比较开,字与字之间间距较大,布局上有大片留白,看上去疏朗大方。这篇铭文代表了当时金文的最高水平,收放自如,章法自然,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周宣王时期,金文已经比较成熟,并且出现不同的风格,毛公鼎铭文以浑厚磅礴知名,而虢季子白盘铭文则以瘦挺精巧出名。
周代作为青铜器和金文的鼎盛时期,佳作自然不止上面提到的几件,其他作品如天亡簋、九年卫鼎、史墙盘、小克鼎的铭文等,都是不可多得的金文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