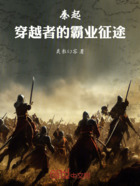
第11章 南荒瘴雾
临淄城破三月后,陈长生接到秦王诏令:着武安君率十万秦军,南下征伐百越。他望着竹简上“骆越之民,断发文身,不服王化”的朱砂批注,指尖摩挲着剑柄上的螭龙纹——这柄随他踏遍六国的鹿卢剑,此刻即将染上岭南的瘴气。
南征军中有三成是齐地降卒,行至丹阳时,已有士兵因水土不服倒毙。陈长生命人在驿站张贴告示,广征熟悉南方地理的向导。一日,有个头戴羽冠的越人少年求见,腰间挂着半块雕着蛇纹的玉玦:“将军,我阿爹说,秦军要过五岭,需经湟溪关,那里的峒主有张‘毒雾图’。”少年说话时,目光始终盯着陈长生的佩剑,似有深意。
“你阿爹是?”陈长生递过一碗粟米粥,少年狼吞虎咽道:“是湟溪关的樵夫,被楚将项燕抓去修城,是将军在郢都放了他。”陈长生想起破楚时,曾释放过一批被征发的百越劳工,不想竟结下此缘。他收下玉玦,任命少年为斥候,赐名“阿蛮”。
五岭腹地,群山如浪。陈长生的战马踏过布满青苔的石阶,忽然听见山风中有竹哨声起伏——这是百越部落的预警信号。他抬手示意全军戒备,只见密林中跳出数十个赤身裸体的战士,浑身涂着靛蓝花纹,手持涂毒竹矛。“勿杀!”陈长生喝止欲放箭的秦军,摘下头盔,露出额间的伤疤:“我曾与你们的峒主合过影。”他指的是在楚地缴获的百越图腾拓片。
为首的战士愣住,盯着他腰间的鹿卢剑穗——那是用百越藤条编织的剑穗,还是阿蛮前日所赠。陈长生趁机用楚语说道:“秦军不来抢粮食,只问一条路:去番禺城怎么走?”战士们面面相觑,最终放下竹矛,领他们绕开了毒雾弥漫的山谷。
抵达湟溪关时,陈长生发现关隘早已废弃,石墙上刻着秦军弓弩手的浮雕——竟是二十年前李信征楚时所留。“看来先王早已属意南扩。”他对副将赵佗说道,“传令下去,在此修筑堡垒,囤积粮草。”赵佗是赵地降将,善抚蛮夷,陈长生特意将他调来南征军。
当夜,阿蛮领着几个峒民潜入军营,献上一坛蛇酒:“峒主说,将军若喝了这酒,就是百越的朋友。”陈长生接过酒坛,闻着刺鼻的药味,忽然想起在临淄时,巴郡士兵送他的平安符。他仰头饮下,辛辣的酒液顺着喉咙灼烧,峒民们发出欢呼,簇拥着他跳起篝火舞。火光中,他看见阿蛮眼中闪过一丝狡黠,却未点破——在这南荒之地,信任有时比刀剑更锋利。
半月后,秦军抵达番禺城下。百越各峒联军据城而守,城头悬挂着用毒藤编织的“拒秦”大旗。陈长生巡视城防,发现护城河中有无数陶罐,里面泡着腐烂的动物尸体——这是百越人惯用的“毒水计”。他命人从上游截断水源,又用投石机将燃烧的艾草投入城中,借南风驱散毒雾。
“将军,他们开城了!”斥候来报时,陈长生正对着舆图研究珠崖岛的地形。番禺城门洞开,峒主们抬着青铜鼎走出,鼎中盛放着岭南特产的荔枝与龙眼。为首的峒主白发垂肩,腰间挂着与阿蛮相似的蛇纹玉玦:“武安君的鹿卢剑,比楚人的血盟更有分量。”他跪下行百越大礼,“愿率五峒子民,归顺大秦。”
陈长生扶起峒主,看见鼎底刻着“越人无岁,与秦为盟”的铭文,忽然想起在临淄城看见的孩童游戏——那些用泥偶演绎六国归秦的孩子,或许永远不会知道,这岭南的青铜鼎里,曾煮着多少代人的血与火。他摘下鹿卢剑,郑重地放在鼎旁:“从今往后,秦与百越,共享太平。”
南征军在番禺驻扎半年,陈长生命人开凿灵渠,连通湘江与漓江,又从蜀地运来桑蚕种子,教百越人种桑养蚕。一日巡视工坊,见几个百越少女用木梭织锦,图案竟是秦军战旗与百越图腾交织,他忍不住笑道:“等织成了,给咸阳宫送几匹,就说这是‘天下一统锦’。”少女们听不懂秦语,却从他的笑容中感受到善意,咯咯笑成一片。
正当岭南渐趋安定,北方传来急报:匈奴头曼单于趁秦军南征,率十万骑兵南下,攻破九原郡。陈长生握着军报的手骤然收紧——他想起在陇西时见过的匈奴骑兵,那些在马背上长大的战士,比百越的毒雾更难对付。阿蛮见他神色凝重,默默递上一竹筒蛇药:“将军,北地的雪,比岭南的雾冷。”
“你随我去北地。”陈长生拍了拍少年的肩膀,“让百越的藤甲,见识一下匈奴的弯刀。”他转身对赵佗交代:“灵渠务必在年内贯通,桑蚕若遇虫害,速报咸阳太医署。”赵佗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忽然明白,这位武安君的心中,从来不止有战场,还有这万里疆域上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子民。
北征的马车驶过长沙郡时,陈长生看见路边有百姓在祭拜“武安君”。土堆前插着木牌,画着鹿卢剑与禾苗——这是他在楚地推行的“兵农合一”政策,让士兵在战后屯田,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他命车夫停下,亲自添了三炷香:“愿你们从此只闻稻花香,不闻战鼓声。”
抵达咸阳时,正值隆冬。秦王政在章台宫召见,陈长生看见殿中多了幅巨大的舆图,六国疆域已用朱笔圈红,岭南与北疆用墨线勾勒,尚未填满。“匈奴屡犯边境,”秦王指着九原郡的缺口,“寡人命你为北地大将军,率三十万秦军,永绝胡患。”
陈长生跪下接旨,鹿卢剑的穗子扫过青砖,发出细微的声响。他忽然想起多年前在新郑当屯长时,梦见自己站在高山之巅,看见千万旌旗汇聚成一个“秦”字。如今,这面旌旗即将插在阴山之麓,而他的使命,也从灭六国变为守天下。
出了章台宫,月光照着咸阳宫的飞檐。陈长生摸了摸怀中的平安符,布包已经磨得发亮,针脚间露出些许棉絮。他忽然想起巴郡的士兵,想起临淄的孩童,想起岭南的阿蛮——那些在战火中相遇的人,那些被他护在身后的百姓,才是他手中长剑的意义。
北风呼啸,吹得宫墙下的铜铃叮当作响。陈长生望向北方,那里有他从未见过的大漠与草原,有需要他用余生守护的边疆。鹿卢剑在鞘中微微震动,仿佛在催促他踏上新的征程。他紧了紧披风,大步走向军营——那里有三十万秦军在等待,等待他们的武安君,带领他们去征服另一片战场,去守护一个叫做“大秦”的梦想。
咸阳城的更夫敲响了子时的梆子,陈长生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这一晚,他没有梦见战火与鲜血,而是梦见了岭南的荔枝树,梦见了临淄的渤海湾,梦见了巴郡的橘柑林——那些他曾用剑守护的土地,正在月光下舒展枝桠,生长出从未有过的安宁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