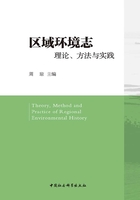
四 考古佐证法
研究环境史,口述资料固然无可替代,但考古资料同样不可或缺。其原因在于,无论是人类记忆,还是文字的记载,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两者都会因人为因素而打乱时空关系。然而,考古资料一旦埋入地下,只要没有经过后人的扰动,所能提供的资料,不仅空间定位准确,而且时间的先后次序也不会错乱。就这一意义而言,考古资料几乎可以充当口述资料和文献资料的最终仲裁依据。但要用好这样的依据,也需要克服观念上和技术上的困难。上文已经提及,处在亚热带丛林中的各民族先辈,都曾经经历过食用桄榔木、芋头和其他块根植物的历史,类似的植物在当代的西南各少数民族实践生活中,还能够找到活态的实证,但是如何用考古资料对相关的生计变迁所引发的生态变迁作出明确的时空定位,进而探明其间的原因,依然是一个重大的难题。
时至今日,涉及食用桄榔木的考古研究资料,在国外的报道中很多,国内的报道仅限于在桂林地区提及这一事实。他们在发掘出来的石器中,确实提取到了桄榔木淀粉的残骸,经过科学验证,完全证实了这一地区的各族先民,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规模性地管护和食用桄榔木。[12]而此前的众多考古调查报告,尽管地层显示的年代下限可以推迟到明清以前,但考古工作者似乎很少人提及桄榔木淀粉的直接证据。究其原因全在于,不少的考古工作者在思想观念上,根本不知道,甚至不敢相信桄榔木可以成为人类的粮食作物,当然也就不会留心到与此相关的考古证据。以至于有关这一事实的考古学证据,事实上是作为垃圾丢掉了,而不是不存在这样的证据,从而使得相关民族的口传资料无法让现代人相信其真实性。这不仅是考古学的损失,也是口述史的重大损失。其次,要从考古资料中提取淀粉,并加以鉴定,相关技术直到20世纪末才引进到考古工作之中。与考古资料相比,传说资料则不同,在苗族、布依族、壮族口述资料中,都能提及一种植物可以食用,但就是不知是哪种树种。与此同时,广西田林地区的壮族却演化出了桄妹和榔男的爱情故事,这样的传说显然与田林地区食用并且出卖桄榔木存在着直接的关联性。但是,上述各种传说由于与国家的财政收入关系不直接相关,直接记载往往告缺,如果不能赋以考古资料的作证,相关传说也只能姑妄听之,无法成为口述史资料去加以利用。贵州黔南地区的苗族则是在创世神话中明确提及他们的祖先与大象和猩猩发生过密切关系,甚至有与猩猩结亲的口述故事,相关的历史记载却无法获得可凭的证据。但有幸的是,不管是在黔南喀斯特岩洞中,还是云南的红河、西双版纳的地层中,都可以找到此前的大象和猩猩广泛分布的证据,比如象牙,猩猩的牙齿等,而且这样的遗骨还与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并存。如果将这样的口述资料和考古资料结合起来,那么有关各民族看上去虚无缥缈的口头传说,乃至荒诞无稽的神话,同样可以成为环境志研究的可凭资料去加以利用。这样一来,环境志研究的资料来源将得到极大的扩充,所能提供的证据的可靠性也可以获得极高的可信度,对环境志而言是如虎添翼。
举例说,西南各民族种植桄榔木、芋头,用刀耕火种的方式种植燕麦和荞子,在西南各民族的传闻中几乎是俯拾即是,而且故事的情节和表述的内容,甚至会同时涉及好几个民族。然而,时至今日,仅凭相关的口述资料要准确考订刀耕火种开始种植小米的时间上限和下限,依然还是一个希望,而无法成为现实。但是此前的考古工作在钻探取样,提取孢子花粉去探讨环境史时,只关注孢子花粉,不关注经过焚烧的炭泥。如果在从事类似考古工作的同时,对混杂的炭泥也展开系统的资料收集,按照不同的时间、空间加以归类整理,那么情况就不一样。因为凭借这样的炭泥,不仅能够确定被焚烧的是什么植物,每一次焚烧的先后次序、间隔的时间都可以通过钻探的土壤样本得到逐一落实。如果在一个坡面的下方,只需钻探五六个土样,那么当地在不同历史时期,通过焚烧哪些植物去种植小米的实情都可以得到逐一查明,使真相大白于天下。相关的口述资料也可以借此被盘活,环境志的研究和文本的编写,也就很能取信于学界同人。毋庸置疑,这将是对环境志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何时能够启动这样的研究,我们将翘首以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