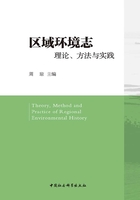
三 书写事象的选择性及切近事实的真实性
由于口述史基本上都是在时间上与自己生活时代距离靠近的“近历史”,对于这种近历史的言说应该与社会生活中需要正视和解决的重大问题相关联,应该树立起人民史观,即并非所有的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是值得书写的。此外,无论是口述史还是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切近历史的真实性都是其存在的重要理由。或者说,真实性是口述史和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的价值所在。同时也必须看到,复调历史的可能性基础也还在于二者的互补性。
尽管口述史书写在近年来赢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正视这些问题并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口述史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
以口述史为名进行的口述记录行动有可能因为赢得市场的需要而放弃了对“口述史之‘人民史观’”的自觉,一味追求对“敏感话题”的聚焦而片面强调名人、伟人的生活秘史或回忆录,[27]因此表现出难以保证其真实性甚至与文献历史相矛盾的倾向。这类所谓口述史因为借猎奇性生产经济利益就极其容易导致罔顾事实的结果。现代生活面临着许多重要的与广大民众利益相关的问题需要解决,而解决这些问题往往就需要对形成这些问题的历史原因进行认真的多方面的探索。口述史在这些原因探索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无论是经验的总结还是教训的汲取都需要多视角的对历史的审视。只有那些与民众福祉相关的选题才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口述史课题。尽管所有的历史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主观成分,然而“选择什么事实”以及“赋予这些事实以什么意义”通常是由“提出的是什么问题”以及研究的前提假设所规定的。进一步地,这些问题与假设同时也就反映出特定时期人们心中最关切的事物,人们所关切的问题随时代的演变而变化。[28]因此,那些以满足猎奇心从而谋取经济利益为宗旨的所谓口述史是不值得提倡的,因为这样的东西可能混淆视听,造成新的矛盾,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
真实性是以口述史和文献为基础的历史的生命保障及价值所在。口述史的真实问题当然也会发生在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书写当中。就口述史而言,如何克服口述者中存在的并非恶意的失真的问题是可以借鉴历史研究方法及滥觞于研究无文字民族的民族志方法的。一般来说,口述史的真实性问题会与口述者的记忆问题有关。口述历史的访谈虽然与新闻记者的采访具有相似性,然而访谈的组织与展开常常需要与其他各类采访进行区分,考虑到受访者“有记忆上的局限”,要求“访谈者和整理者大胆介入,用相关文献的补充与互证口述史料,纠正受访者记忆的失误”。[29]这与民族志工作中必须在访谈前对相关问题进行资料准备相一致。访谈者事先对相关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以及对问题有深入的把握是十分必要的。民族志工作中的文献法是来自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的方法,这一方法理应有助于口述史的发展。
口述史方法虽然“使得历史的认识过程”增加了“受访者与历史现象间的关系、访问者与受访者间的关系”两个新维度,但口述访谈中采取行之有效的、能够妥善处理好“这两个关系”的方法是亟待探索的。[30]对访谈人的选择是否合适在一定程度上会决定口述史价值的大小。一般来说,那些对历史事实有较为全面了解的人,尤其是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是较为理想的访谈对象。此外,在访谈工作的开展中借鉴民族学家特别重视的参与观察法也是重要的。虽然,采访者不可能和受访者再去重新经历一次历史的过程,但采访者经过与受访者一段时间的相处,熟悉受访者的生活习惯,并对受访者的思维表达习惯有相当的了解对于访谈工作的开展会是十分有益的。对受访者的深入了解还是确定采取结构式访谈、半结构式访谈还是其他访谈方式的重要依据。
民族志工作中主位与客位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于口述史工作来说也是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的。在民族志工作中,主位研究是指研究者尽量克服自己的主观认识,尽可能地从当地人的视角去理解当地人的文化,把当地人的描述和分析作为最终的判断。客位研究是研究者从文化外来观察者的角度来理解文化,用比较的和历史的观点看待民族志提供的材料。主位客位方法的结合是民族志研究者调查的基本方法。在口述史的采访与受访者之间,充分尊重受访者的表述并对这样的表述做出尽量客观的分析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说民族志“从根本上讲是在理解各种文化拥有者基于各自文化而进行的有关文化的共同阐释的阐释”[31]。那么由采访者和受访者共同完成的口述史也是两者基于各自的历史视角而进行的有关历史的共同阐释的结果。
当口述被视为一种言说活动,那么言说活动的深层目的则需要被加以考量。演唱哈尼迁徙史《哈尼阿培聪坡坡》的歌手这样唱道,“祖传的古经,是真的我没亲眼见过,是假的我说不清,我把先祖的古歌传给后人。”在谦虚的表白之后,歌手基本是按他自己认为真实的历史来唱的。但是,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民族之间互相帮助的现实还是影响到了他的演唱。朱小和将那些记恨汉人的内容一两句就带过,省略这些在他看来是不利于今天的民族团结的内容是应该的,这也是他对新时代新生活的充分肯定的结果。在整理者史军超不断解释那些民族之间存在矛盾乃至仇恨都是过去的事情,并不会对现在产生不良的影响,直到疑虑被打消后,朱小和才把那部分细节补充完整。[32]从这个事情中可以看到,人们在进行表达的时候并不会对于任何信息不加筛选地传递出去。人们是依照自己的观念有选择地对信息进行甄选并不断利用这些信息构成自己的知识体系与价值观念的。
此外,就采访者而言,充分意识到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可能存在的文化图式的差异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除了采访者与受访者可能出自不同的社会文化而产生文化图式的差异之外,采访者与受访者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以及处于不同的时代,都有可能造成两者之间的文化图式上的差异。“在民族志工作中,要更好地认识与表达多元的世界,就必须认识到,作为传递信息的语言及人的世界的界限是多样性的。人们是以作为思维与直观的中介的图式去同化与整合生活经验的。在多元的生活世界中,文化图式的跨文化转喻是实现跨文化理解的一种认识与表达方式。”[33]受访者与采访者使用不同母语而引起文化图式的不同以及口述工作将口述材料转写为文字并出版发行等等因素而造成不真实的情况。[34] 在采访者和受访者中存在文化图式的差异的时候,跨文化转喻的方法就是必不可少的。所谓跨文化转喻是指“以一种文化中的图式与另一种文化中的图式相联系来生产转喻,从而获得对他者文化的理解……在不同的文化间进行的图式转喻是否真正有助于跨文化理解,取决于民族志工作者对于自身文化图式及他者的文化图式的理解是否深入”[35]。对于口述史采访者而言,对于自身文化图式是否自觉以及对受访者的文化图式的理解是否深入直接影响了表达与接受之间的困难能否真正克服。
毫无疑问,口述史并不等于民族志,相对成熟的民族志工作方法可以为口述史工作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在口述史的发展过程中,汲取包括民族学在内的其他学科的经验是必要的,但更加积极地探索能够更加适合自身发展的新方法是更加必要的。这也应该成为口述史实践者的自觉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