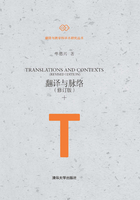
四、译者的角色
简言之,翻译就是语言的再现,而翻译者就是语言的再现者(representer)。萨义德(Edward W. Said)借用福柯(Michel Foucault)有关知识、论述、权力的观点,一再阐释再现的意义并落实于古今例证的探讨。 有意义的是,在标举“代表/再现”为书名的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中,萨义德(Said, 1994: xv,11,12,14,113)特别明指知识分子在代表/再现他人时,其实也代表/再现了自己。
有意义的是,在标举“代表/再现”为书名的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中,萨义德(Said, 1994: xv,11,12,14,113)特别明指知识分子在代表/再现他人时,其实也代表/再现了自己。 我们据此引申:作为再现者的译者(也是某种意义的知识分子——至少是具备两种语言知识的人),在代表/再现原作(者)时,其实也代表/再现了自己。
我们据此引申:作为再现者的译者(也是某种意义的知识分子——至少是具备两种语言知识的人),在代表/再现原作(者)时,其实也代表/再现了自己。
我们或可据此将译者的角色姑且区分为显性与隐性两种。这里所谓的显性是指代表/再现原作(者)的译者,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名正言顺、堂而皇之地作为以另一语言来呈现原作(者)的工作者之身份出现,而译作便是兼具作者和译者名号的文本。反之,所谓的隐性则指透过译本所代表/再现的译者,也就是以往不受重视、隐而未现的译者——有时甚至连真实姓名、身份都不为人知。在观察与省思译者的隐性角色时,读者多少得花一些阅读、考证、发掘的工夫,才较能察觉译者所采取的翻译/再现策略和手法。这些翻译/再现策略和手法中,较突出的是外加于原文文本之上的文字,如译序、译注、前言、后记甚至访谈、参考资料等。这些既是译者对文本与读者的(额外)服务,也代表了译者对文本与作者的认真负责,以期在正文之外更进一步再现作者。 至于隐入正文文本的部分,如措辞、句法等,则需要具有双语和批判能力的读者/批评者耐心对照原文或比对其他译本,以发掘译者在实际翻译过程中的决策与抉择,其中大至通篇文体的选择,小到一字一词的译法,都是可以仔细探讨的对象。
至于隐入正文文本的部分,如措辞、句法等,则需要具有双语和批判能力的读者/批评者耐心对照原文或比对其他译本,以发掘译者在实际翻译过程中的决策与抉择,其中大至通篇文体的选择,小到一字一词的译法,都是可以仔细探讨的对象。
前文提及,译者的成品既再现了原作(者),也再现了身为译者的自己,因此译者基本的角色既是原作(者)的再现者,也是译者的自我再现者(self-representer)。我们可由此出发,试图进一步讨论可能涉及的不同面向和角色——虽说其中难免有界线模糊、不易厘清之处。
首先当然就是中介者(mediator)的角色。译者身处不同语言与文化之间的中间位置(in-between status),凭借着语言与文化能力(linguistic and cultural competence)成为二者之间的沟通者(communicator)与传达者(expresser),将原作根据译者的能力、意图与其他相关条件,以另一种语言呈现。 这种角色的基本认定在于沟通与传达,往往显得相对低调,仅在可能的范围内将原文“原汁原味”地呈现,以期达到异文化之间信息的传递与了解。这种译者即使有使命感或表现欲,也无意凸显自己的角色,反而务求化入译文中,以平实的再现方式扮演异语言与异文化之间的传达者与沟通者。这大抵是一般对译者的基本期许。
这种角色的基本认定在于沟通与传达,往往显得相对低调,仅在可能的范围内将原文“原汁原味”地呈现,以期达到异文化之间信息的传递与了解。这种译者即使有使命感或表现欲,也无意凸显自己的角色,反而务求化入译文中,以平实的再现方式扮演异语言与异文化之间的传达者与沟通者。这大抵是一般对译者的基本期许。
相对于前者的低调,另一种再现者的角色较为明显,使人不但注意到译文所呈现的原作内容,也注意到译者所选择的再现方式,因而更彰显了译者的自我再现。换言之,译者为了使译文成为传达特定意图与信息的工具,而选择积极介入,即使译文依然宣称或试图忠实于原文,但附加其上的意图和方式使得译者成为相当程度的介入者(intervener)甚至操控者(manipulator)。以“信、达、雅”“一名之立,旬日踟蹰”等说法闻名的严复,在翻译史密斯(Adam Smith)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时,除了译文之外,还增添了310条、长达数万言的案语。赖建诚(2002:74—76)将这些案语归为七类:“说明译书时,书中所谈之情境已有变迁者”“补充原文之说明者”“评论原文说法者”“以中国式说法与原文相比较者”“以中国经济与欧洲相比拟者”“借洋之例以喻中国之失者”及“译自Thorold Rogers教授之注语者”。此外,尚包括了“对史密斯的批评”“谈论不相干的政权与宗教问题”及“个人的读后感”,而且“他的案语中有许多是夹杂式的,是随感的、无系统的,或是个人感怀的”。如此看来倒像是将中国固有的评点应用于译文上,这些反而成为研究《原富》的再现者严复的重要素材。而严复积极介入译文,不但是中国翻译史上的异数,也成为研究晚清思想史的另类素材。
这类翻译往往发生于启蒙初期或信息相对欠缺的时代,在一般人不易取得相关信息的情况下,译者的使命感或教育感骎骎然有凌驾之势,借由夹译夹议的方式,假借译文夹带自己的见解与议论,深深介入文本之中,“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以致产生一手/译手遮天的现象。傅大为(2003:17)便指出:“这种所谓夹译夹叙的二成空间(其余八成为翻译)……过去的知识分子,从严复到殷海光,都很优于利用这个二成的策略空间;打着翻译西学的名号,其实却常按着自己的意思,在‘译着’(又译又着)西学”。因此,原文的翻译固然有其特定意义,但译者的理念、再现策略、译文在当时社会与文化脉络中所产生的效应以及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其重要性可能不亚于译文本身。笔者以为,这种文本或可称为“‘译者式的’文本”(“translatorly”text)。
再者,译者也具有背叛者(betrayer)、颠覆者(subverter)、揭露者/掩盖者(revealer/concealer)以及能动者/反间(agent/double agent)的角色。由于翻译是在另一个语言脉络中的再现,势必产生衍义/衍异的现象,“完全忠实”只是不可企及的迷思或妄想,只要读者有心,小从一字一词,大到整个文本,都可解读出与原文落差之处,因此扭曲或误译不但“查有实据”,而且往往“事出有因”,以致译者不但难逃背叛、颠覆之讥,甚至可能在背叛、颠覆原作(者)的同时,也自我背叛、颠覆。
其次,由于原文无法充分了解、完整传达(甚至对“充分”“完整”的判断标准也莫衷一是),译文本身的衍异又层出不穷,以致翻译中同时出现“揭露”与“掩盖”的现象。此处的“揭露”一方面指将原文之意透过另一个语言表达,另一方面则是译文在另一个语言与文化脉络中出现时,产生意想不到的含义与效应(或可称为“原作的潜能”)。至于“掩盖”,依先前“Traduttore, traditore”之例,可以看出小至一字一词的形、音、义,大至整个观念和文本在另一个文化及历史脉络中的再现,都必然有不尽周全之处,译者之左支右绌源出于此,只能尽己之力,挖空心思,试图表达、“揭露”原意,或改弦更张,发掘、“揭露”潜能,以求补偿。
译者表面上看来再如何消极、被动,但身为译文的生产者(producer)之关键地位毕竟不容否认,套用先前有关翻译空间与时间的比喻,他在移译的过程中发挥着搬运者(carrier)与言说者(speaker)的作用,即使其功过难定,但费心劳力之处肯定有之。因此,身为语言的转换者(transformer),促使原文的文本以译文出现,其本身就是一个能动者。而在所从事的工作中,由于无法避免前述的揭露与掩盖,所以具有相当的运作空间,来遂行译文的再现,甚至有意无意间进行颠覆原意的工作,如此一来,则又扮演了“反间”的角色,至于结果是好是坏,各人根据不同的立场、角度与标准,往往见仁见智。
严格说来,每位译者多多少少都扮演了背叛者/颠覆者、揭露者/掩盖者、能动者/反间的角色,然而其中也有弱势与强势之分。再者,有意的违逆者也有可能为了达到目的而特意伪装,貌似忠实,却另有图谋。以下所举两例虽为虚构之作而且事涉口译,但多少可视为将这种情况推到极致所可能产生的现象,自有值得思索之处。
越南裔美国女作家高兰(Lan Gao, 1997:21)在《猴桥》(Monkey Bridge)中描写越南难民移居美国的困境,第二章提到越南母亲命令女儿向美国公寓经理要求更换公寓,原因是现在的住所直冲对街屋顶上的大天线,风水不佳,会招致不测(“它的长杆架直接瞄准我们的起居室,有如一柄致命的剑,威胁着要把我们的未来和健康劈成两半”)。虽然母亲振振有词,但女儿知道这个理由实在难被异国人士所接受,在母命难违的情况下,只得运用“我的新世界伎俩”,向经理谎称公寓内有蛇出没,而得以换房,达到母亲托付的任务。换言之,身为居中传译者的女儿编造理由,当面欺瞒言语不通的双方,在一问一答之间达到受委托的目的。另一例则是黄春明(2000:10—72)的名作《莎哟娜啦·再见》里的黄君,虽然在故事中的处境类似买办、皮条客,却也在旅程中伺机运用身为中间人的语言优势,竭尽操弄之能事,在七个日本买春客和一个台大中文系四年级学生之间“搭了一座伪桥,也就是说撒了天大的谎”,明为口译,让双方意见得以交流,暗地却大肆扭曲传译的内容,“藉这个机会刺刺日本人,同时也训训我们的小老弟”,由原先的“恶作剧”,进而“两边攻打”“作弄着两边”,直刺彼此的痛点,使得双方颇感愧疚,而多少弥补了黄君因其处境而丧失的自尊。
此外,译者也扮演了“re(-)placer”的角色,此处取“re(-)place”之“重置”与“取代”之意。就“重置”而言,译者透过翻译行为把原文的位置由一个语言与文化脉络移转并重新置放于另一个语言与文化脉络。就“取代”而言,在新的语言与文化脉络中,译本作为原本的再现,成为译入语的读者据以了解原作者旨意的重要凭借——对不懂原文的人来说,往往是唯一凭借。只要想想,古今中外有多少人能以原文阅读圣经或佛经,便知先前有关“总是已经被翻译了”的说法绝非夸大其词。尤有甚者,在原文佚失、渺不可得的情况下,译本还可能被当成原始文本(source text),或译回原文,或进一步译成其他语言。如中国的佛经翻译经由译场的层层作业、严格把关,在译出汉文、多方确认无讹之后,有时竟销毁原文,以确立译文的权威。而原为梵文的许多佛经,因为在印度失传,有时反得将汉文译本翻译/回译成梵文,以兹保存与流传。至于将已失传的梵文佛经,由汉文译成藏文、日文、英文等,或由藏文译成汉文、日文、英文等,都是进一步的重置与取代。
最后,站在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译者更扮演着脉络化者(contextualizer)以及——在理想的情况下——双重脉络化者(dual contextualizer)的角色。这里所谓的“脉络化者”最单纯的解释就是,译者透过翻译把原作引入另一个语言与文化的脉络。然而,在这么做的同时,若能积极介入,进一步引介与评述有关原作和作者的背景及意义,以便读者将此一特定文本置于作者的个人及历史、社会、文化脉络中,当更可看出原作在其脉络中的意义。再就“双重脉络化”而言,译者身为与原文文本挣扎、转换为译文文本的工作者,对两个文本的字字句句以及语言转换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拥有一般读者无法得知的事实与无可比拟的感受,此一“特权”(有时可能是“切肤之痛”)自有其文化移转(cultural transference)上的意义。因此,若能清楚交代为何及如何在此时此地有如此译本产生,固然能协助当代读者看出翻译过程的甘苦、译本与自己的相关性(relevancy)及时代、文化意义,也能为后代读者保留有关译本的第一手资料,彰显译者所扮演的诸种角色。 再者,对实际从事翻译的学者而言,也可看出其以学术为基础,一方面介入文本与文化的翻译,另一方面以翻译作为介入社会的工具,借由译本达到学术作为介入(scholarship as intervention)或介入式的学术(interventionist scholarship)之期许。
再者,对实际从事翻译的学者而言,也可看出其以学术为基础,一方面介入文本与文化的翻译,另一方面以翻译作为介入社会的工具,借由译本达到学术作为介入(scholarship as intervention)或介入式的学术(interventionist scholarship)之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