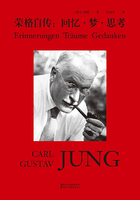
第3章 童年(2)
当时什么在我心里言说?谁言难题而胜人一筹?谁把上界下界组合起来,以此定局,使我后半生充满狂风巨浪?谁让人心情浓重地预感人生成熟岁月而搅扰了纯真无邪、无所苛求的童年?除了来自上界、下界的生客,岂有他人?
这个孩童之梦向我透露了尘世的秘密。当时可谓埋入地下,过了许多年,我才走出来,如今知道,这么做是为了尽量发蒙启蔽(烛幽发隐),这是一种进入黑暗王国的仪式。那时,我的精神生活无意识地开始了。
我不记得1879年我们迁往巴塞尔市附近的许宁根小镇,但清楚记得几年后发生的一件事:晚上,家父让我下床,抱着我登高走进朝西的凉亭,让我看神丽至极的绿色中闪耀的夜空。那是1883年喀拉喀托火山爆发之后。
还有一次,家父带我去野外,让我看东方天际线上的大彗星。
一次发大水,流经村庄的维瑟河决堤。上游有座桥垮塌,十四人溺亡,黄水把他们冲向莱茵河。据说,洪水消退,尸横沙滩。我就不能自持了。我发现一个中年男子的尸体,身裹黑色礼服大衣,显然刚出教堂!他沙土半掩,屈臂遮眼。令家母震惊的是,旁观如何杀猪也让我着迷。对我而言,所有这些事都极富趣味。
我对造型艺术最早的记忆也延伸至在许宁根小镇的那些岁月。在父母家、18世纪建造的那幢牧师楼里,有一个陈设庄严的昏暗房间。那里家具精良,墙上挂着古画。我尤其记得表现大卫和歌利亚的意大利画作。那是圭多·雷尼工作室的复制品,原作挂在卢浮宫,不知如何到了我家。还有另一幅古画挂在那里,现在我儿子家里;那是19世纪初的巴塞尔景色。我常常潜入僻静的幽暗房间,在画前坐上几个小时,端详这种华美。那确曾是我所知的唯一美事。
那时我还很小,约六岁,一次,一个阿姨带我去巴塞尔看博物馆中的动物标本。我们在那里流连良久,因为我想端详一切。四时左右,响铃表示博物馆要闭馆了。阿姨催促着,我却跟陈列橱难舍难分。在这中间,展厅锁上了,我们不得不走另一条通往台阶的道路,穿过古代艺术品游廊。突然,我站在这些美妙的形象之前!我陶醉地瞠目而视,因为还从未见过如此美物,百看不厌。阿姨扯着我的手往外走,我总是落后一步,她喊道:“臭小子,闭眼!臭小子,闭眼!”在这一刻,我才注意到,那些形象祼身持无花果叶!我先前根本没见过。我就如此与文艺初相遇。我阿姨大为光火,似乎有人带她偷偷穿过色情场所。
六岁时,父母带我去阿里斯海姆市远足。趁此机会,家母穿了一条连衣裙,我一直难以忘却,它同样是我唯一记得的她的连衣裙,那是一块黑衣料,印有绿色小半钩月。在这幅最早的回忆画面中,家母显现为苗条少妇。在我的记忆中,她始终较年长、丰满。
我们来到一座教堂,家母说:“这是天主教堂。”我的好奇心混杂着焦虑,使我逃离家母,要透过敞开的门往里看个究竟。我正看见装饰得富丽堂皇的祭坛上有大蜡烛,突然在台阶上绊倒了,下巴撞上了刮削器。我只知道,父母把伤口鲜血淋漓的我提溜起来。我的心境匪夷所思,一方面因喧嚷而引来礼拜者注意而羞惭不已,另一方面觉得犯戒了:耶稣会士—绿帘—食人者的秘密……这就是天主教堂,与耶稣会士有关。我绊倒、喊叫,都是他们的过失!
我累年不再踏足天主教堂,不再暗自害怕血、跌倒与耶稣会士,这是他们云山雾罩的色调或氛围,但它始终令我神往,接近天主教司铎也许更不舒服。三十几岁时,我步入维也纳斯特凡大教堂,才能不费力地感觉到教堂之母。
六岁,由家父授课,我开始学习拉丁文。我并非不愿上学,因为总是领先于其他人,学校里的课程让我觉得容易。我入学之前,已能识文断字。还记得尚不识字时,缠磨家母给我朗读,而且是选读一本旧童书《世界图解》(Orbis pictus)[1],其中表现了异国情调的宗教,尤其是印度教。书中有梵天、毗湿奴与湿婆的插图,使我兴味盎然,源源不竭。家母后来说,我反复提及它们。我隐约觉得近似于我从未与人说起过的“原始天启”,它是我不可泄露的秘密。家母间接证实了我的想法,因为她说到“异教徒”时轻蔑的口吻逃不过我的耳朵。我知道,她会震惊地拒斥我的“天启”。我不愿遭受此类伤害。
这一少年老成的举动一方面与高度敏感、极易受伤相关,另一方面尤其与我只身孤影有关(舍妹比我年幼九岁)。我以自己的方式独自嬉戏。可惜,我想不起玩过什么,而只记得不愿受搅扰,沉醉于自己的游戏,受不了遭人注视或评判。我还忆起,七八岁时热衷于搭积木建塔,狂喜地用“地震”摧毁它们。八至十一岁,我无休无止地描画征战场面、围攻、射击,还有海战。于是,我画满了一整本墨迹图,沾沾自喜于对它们做信马由缰的解释。学校之所以可爱,是因为我在那里终于找到了朝思暮想的玩伴。
我还找到了别的什么,引发我稀奇古怪的反应。在讲述之前,我想提及的是,夜的气息渐浓。焦虑之事、不解之事,万事皆生。父母分房而眠,我睡在父亲房里,母亲令人焦虑不安的影响力穿门而来。夜间,母亲阴森可怖、神秘莫测。一夜,我看见从她门里走出一个模糊不清的发光人物,前冲的脑袋由脖子衬托出来,在空中飘浮于前,犹如细月。即刻形成一个新头,又自我突出。此过程重复了六七次。我做了忽大忽小之物的噩梦,比如远处小球,逐渐接近,一边长得硕大无朋,或者鸟栖其上的电报线。电线越来越粗,我越来越怕,直到惊醒。
虽则这些梦基于生理上正在酝酿的青春期,它们仍有前奏,大约是在十七岁时。当时,我罹患哮鸣性喉痉挛,继发窒息。发作时,我站在床尾,躬身向后,家父抓住我腋下。我看见头上有望月大小的蓝色光圈,金色人物移步其间,我以为是天使。此种幻象次次都平息了对窒息的焦虑,梦中却再度浮现。我觉得精神性因素此时起了决定性作用:精神氛围开始变得不宜于呼吸。
我百般不愿进教堂,圣诞日是唯一的例外。圣诞赞美诗“这是上帝择定之日”深合我意。晚上来了圣诞树。这是我热烈庆祝的唯一基督教节日,其他诸节,皆淡然视之。第二位轮到除夕。基督降临节别具风味,这种风味与即将到来的圣诞就是不甚协调,事关夜、天气、风,也与宅中昏暗相关。有什么喃喃低语,有什么出没作祟。
与幼年那时重合的是在与乡间学友来往时的发现,他们使我异化。我与他们在一起时与独自在家时不同。我一同捣蛋,或者自己想出在家时似乎从未想到过的恶作剧。虽然我太知道自己单独在家也可能憋出各种花样来,但觉得自己因同伴的影响而改变,他们有点引诱我,或者迫使我不同于自己以为的模样。我在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时结识与父母不同者,我觉得它的影响若非可疑,也成问题,而且隐含敌意。我愈益感知晴天丽日之美,此时“金晖闪耀,绿叶婆娑”。就在旁边,我却预感到一个不可否认的暗虚世界,有无法回答的疑问令人担忧,自觉在劫难逃。我的夜祷正式结束白天,使天入夜,使人入眠,它虽然给我程式化的保护,新的危险却潜伏于日间。似乎我感觉、担忧自己一分为二,内心的安稳遭受威胁。
记得这段时间(七至九岁)我喜欢玩火。我们园子里有巨砾垒成老墙,其隙形成奇洞异穴。我往往续上一处小火,此时,其他孩子帮我,须是“长”明火,因此,须始终续火。为此,需要我们齐心努力,搜集所需木柴。除了我,无人可以照管这把火。其他人可以在其他洞里点火,但这些火是凡俗的,与我无关。唯有我的火是生龙活虎的,有明白无误的明光意味。当时,这是我长期的心头好。
从这道墙延展出下坡,嵌着一块石头,有点外凸,这是我的石头,独处时,我常常坐上去开始游思浮想,大致如此:“我坐在此石上。我在上,它在下。”石头却也可能说“我”并且想:“我在此,在这坡上,而他坐在我上面。”于是提出的问题是:“我是坐于石上者还是有人坐在我上面的石头?”此疑问总是使我迷惘,我就起身,一边怀疑自己,一边穷究现在谁为何物。这一直不明不白,我忐忑不安,伴以引人注目、令人神往的模糊感。毋庸置疑的事实却是,此石与我有神秘关系。我可以在上面一坐几小时,着迷于它给我出的谜。
三十年之后,我又站在那片下坡上,已婚有子,有房,在世上有一席之地,满脑子想法与计划,我忽又成为那个孩子,燃起充满神秘意味的一把火,坐于石上,不知它是我抑或我是它。忽而想起在苏黎世的生活,觉得很陌生,就像来自另一世界、另一时代的音信,诱人又骇人。我正沉迷于其中的童年世界恒久不变,而我挣脱了它,堕入一个滚滚向前、渐行渐远的时代。为不失去未来,我不得不勉强自己掉头离开此地。
这一刻难以忘怀,因为它让我对童年时光的永恒特质豁然开悟,这种“永恒”意指为何,随后就在十岁时表现出来。我在辽阔世界中一分为二、忐忑不安,使自己采取当时费解的举措:那时使用一个黄漆皮匣,带一把小锁,初级学校学生都有。里面也有一把直尺,我在末端刻上高约六厘米的小人,着“礼服、礼帽与乌亮鞋子”。我用墨水把它染黑,从直尺上锯下,放入皮匣,我在匣中给他备下小床,甚至用一块毛呢给他做了一件小大衣。我放了一块光滑、微黑的长形莱茵卵石,涂上五光十色的水彩,使它分成上下两部。它长久在裤袋里陪伴着我,这是他的石头。整件事对我是个大秘密,我却不解其意。我把装着小人的匣子悄悄放到禁入的顶楼上(禁入是因为阁楼木板生虫腐烂而危险),藏到屋顶架的支梁上。我感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无人会看见。我知道,那里谁都找不到。无人会发现、摧毁我的秘密。我觉得保险了,排遣了与我自己一分为二的受罪感。
每当我干了什么;或者伤及痛点;抑或家父神经过敏、家母病体恹恹,让我备受压抑;在所有这些困境中,都想到我那细心安顿、包裹的小人和他那块粉饰过的光滑石头。时不时(常常间隔好几周),而且只在确定没人看见我时,悄悄登上阁楼,爬上房梁,打开匣子,端详小人和石头。每次都放进一个事先在上面写上什么的小纸卷,是我上课时用自己编排的密码写的。那些小纸条,写得密密麻麻,卷起来交给小人保管。我记得,放入小纸卷的仪式始终具有庄严性质。可惜我想不起来,要告诉小人什么,只知我的“信”对他意味着一种藏书。我推度,可能是尤合我意的某些格言警句。
此举的意义,或者我原本可能如何说明此事,当时并非问题。我限于新获安全感,满足于占有无人触及、无人知晓者。对我而言,这是牢不可破的秘密,永远不得泄露,因为我的存在是否有保障取决于此。为何,我不自问,就是如此。
拥有如此秘密,当时强烈影响了我。我视之为少年岁月的根本,对我至为重要者。所以,从未向人讲述青少年时的阳具梦,而且,连耶稣会士亦属不可言及的阴森王国。小木像连同石头是童年尚未自觉地首次尝试打造秘密。它总是摄魄勾魂,我感觉应该寻根究底;不过,不知我欲表达者为何。我始终希望,可以发现什么,或许在自然中,会予人启示,或者示人秘密何在或何为秘密。彼时,对飞潜动植与石头兴趣日增,不断寻找神秘莫测之事。在意识上,我是笃信基督的,哪怕打了折扣,“但不那么确定!”或者问道:“地下之物怎么办?”每当有人向我灌输宗教教义,对我说这好那好,我就心想:“是,可还有其他十分秘密之事,而大家都不知。”
刻像插曲构成我童年的顶点与终结,持续约一年。此后,对该事件记忆尽失,直到三十五岁。从云山雾罩的童年中冒出一段清晰无比的记忆,我当时忙于《力比多的转变和象征》一书的前期工作,讲述阿里斯海姆市附近的灵魂石密藏(Cache)和澳大利亚人的雕图护身符。我突然发觉,对这种石头有确定印象,虽则我从未见过图片。在想象中,我看见一块光滑石头,涂成上下两部分。我觉得这幅图景有点面熟,还伴随着忆起微黄的皮匣以及小人。小人是希腊罗马文化时期裹得严实的小神泰莱斯福鲁斯,他在某些古画中立于医神埃斯科拉庇俄斯身旁,给后者朗读书卷。
有了这次重拾记忆,我初次确信,有些原始心灵要素不可能出于传统而深入个体心灵。因为我还是(nota bene)很久以后才细看了家父的藏书,其中没有一本包含此类信息。确实,家父对此类事物亦一无所知。
1920年,我在英国时,用细枝刻了两个类似人物,根本不记得童年经历。我把其中一个放大雕成石像,而此像现在立于屈斯纳赫特镇上我家花园里。那里,潜意识才促发我命名它,称其为“气韵生动(Atmavictu)”——“breath of life”。此像进一步发展童年那个准性对象,后者后来却表明是“活力(breath of life)”,是创作冲动。这一切其实是卡比里[2],裹着小大衣,蒙在“盒子”里,配备活力储备器、长形微黑的石头,这却是我很晚之后才澄清的关联。童年时遭遇此事的方式与以后在非洲土著人处看见的一样,他们先这么做,全然不知在做什么;很久之后,才沉思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