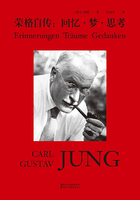
第17章 疗救心灵(3)
然而,心理治疗师必须理解的却不仅是患者,理解自己同样重要。所以,教育必不可少的前提是自我分析即所谓训练分析。对患者的治疗可谓在医生身上开始;只有懂得与自己打交道、处理自身的问题,才能教会患者也如此行事,但只有到了那一步才行。训练分析时,医生须学会认清并认真对待自己的心灵,若做不到,则患者也学不会,但他就此缺损一块心灵,正如医生也失却自己不了解的那块心灵。因而,医生在训练分析时掌握一个概念体系还不够,作为精神分析对象,须认识到,分析涉及自己,它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而非(字面意义上!)可以熟记的方法。医生或者治疗师在训练分析时不领会这点,以后必将会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虽然也有所谓“小型心理治疗”,但真正分析时,要求患者和医生全身心冲破障碍。有许多不自我牺牲就无法痊愈的病例。若触及要事,则关键是医生是否把自己看成事件的一部分,还是把自己打扮成权威。在人生的重大危机时,在紧要关头,事关生死存亡,这时诱导性的招数于事无补,医生连同其生存都遭遇挑战。
治疗师须随时向自己说明如何对与患者的对立做出反应,不仅用意识做出反应,而且须始终自问:我的潜意识如何体验此情境?也就是须尝试理解自己的梦境,密切注意,观察自己与患者,否则,整个治疗可能走样。我想给您讲个事例。
我曾有个患者,一个非常聪慧的女士,但由于好些原因,让人觉得可疑。起先,分析进展顺利,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解梦时似乎不对头了,以为察觉到谈话肤浅了,所以决定跟患者谈谈,因为,有什么事不正常了,当然也逃不过她的眼睛。在下一次就诊前夜,我做梦如下:
夕晖中,我漫步在乡村道路上,穿过山谷。右边是陡峭的丘陵,上面矗立着一座宫殿,最高的尖塔上,一名妇人坐在栏杆之类的东西上。为了能看个真切,我不得不后仰,脖颈一阵痉挛,于是就醒来了。还在梦中,我就认出,那名妇人是我的患者。
我立刻就明白如何解梦了,在梦中不得不以此方式仰视患者,实际上十有八九鄙视她。梦境确是对清醒态度的补偿。我把梦境和自己的解释告诉她,马上导致局面改观,治疗又顺畅了。
身为医生,我不得不始终自问,患者给我带来何种信息?患者对我意味着什么?若他无关紧要,我就没有弱点。只有在医生自己的痛点上,患者才产生影响,“久病成良医”。但医生穿上人格面具的铠甲时,患者不起作用。我认真对待患者。或许我与他们一样面临问题。确实常常发生的是,患者恰恰是适合医生弱点的对症膏药,由此可能也给医生,或者恰恰给他造成困境。
每名治疗师应由第三者督导,这样还能保有另一视角。即使教皇也有忏悔神甫。我总是劝告分析师:“找个‘忏悔神父’或者‘忏悔嬷嬷’吧!”因为妇女们有此天分,她们的直觉常常出类拔萃,评价一语中的,能够看穿男人,也许还有他们的女性意象诡计。她们看得见男人看不到的方面。所以,还没有妻子坚信丈夫是超人!
若有人得了神经症,理所当然要接受分析;但若他“正常”,则不存在此类强迫。然而,我可以向您保证,关于正常状态,我有过令人惊奇的体会,曾遇到一名完全“正常”的从医的弟子,他是医生,给我带来一名老同事的问候,他曾是后者的助理医生,接手了诊所。他事业有成,一如常人,诊所普普通通,妻子平平常常,子女身心健康,住在寻常小城常见的不大的房子里,收入一般,很可能饮食也无特别之处!他想成为分析师,我告诉他:“您知道意味着什么吗?这就是说,您得先了解自己,工具就是您自己。若您不对头,那患者如何可能变得对头?若您不自信,如何能让他信服?您自己得是真材实料。但若您并非货真价实,那就但愿天助您!您会把患者引入歧途。您先得主动分析自己。”——此公赞同,但马上对我说:“我没什么棘手事可说!”这本该令人警觉。我说:“好吧,那我们可以看看您的梦境。”他说:“我没做梦。”我道:“您很快会做梦的。”要是别人十有八九就会在紧接着的夜里做梦了。他却不记得做过梦。大约过了两周,我觉得不祥了。
最后,出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梦。他梦到乘火车,列车在某个城市停留两小时。因为做梦者不熟悉此城,又很想了解,就去了市中心,他在那里看见一幢中世纪房屋,很可能是市政厅,就走了进去,穿过长廊,踱入美室,墙上挂着古画和织花壁毯,古玩珍宝随处摆放。他蓦地瞥见天黑日落,心想:我得回火车站了!——此时此刻,他发现自己迷路了,不知何处是出口,吓了一跳,同时意识到在这幢房子里没有遇到过人,他毛骨悚然,加快步伐,希望遇上什么人,但什么人也没遇见,于是走向大门,如释重负地心想:那就是出口!——他打开门,发现置身于一间巨室,暗得连对面墙壁都看不清。他大吃一惊,飞跑着穿过开阔空荡的房间,因为希望在厅堂的另一侧找到出口。这时,他看到——就在房间中央——地上有白色之物,近前才发现是约莫两岁的痴儿坐在夜壶上,浑身粪便。在此瞬间,他大叫一声醒来,心慌意乱。
我就很有把握了:这是潜在的精神病!我可以告诉您,尝试让他脱离梦境时,我出汗了。我不得不尽可能把此梦境说得没有大碍,根本不探讨细节。
梦境所述,大致如下:开头的旅行是前往苏黎世,但他在那里只是短暂停留。处于中心的孩子是他自己两岁时的形象。对幼儿来说,如此不良之举虽然不同寻常,但还是可能的。粪便吸引他们关注,因为有颜色、有气味!若儿童在城里长大,可能还是在家教严格的家庭里,就容易出现这种事情。
但做梦的那个医生并非儿童,他是成人。所以,位于中心的梦中形象是禁忌的象征。他讲述梦境时,我就明白,他的正常状态是一种补偿。我在最后一刻逮到他,因为潜在的神经症差一点暴发并且变得明显,必须阻止。最终,借助他的一个梦,给训练分析找到可以服人的结局,我俩都感谢有此结局。我不让他知道我做的诊断,但梦境告诉他有危险的精神病人纠缠时,他可能察觉正在接近慌乱,后果严重。做梦者旋即返回故乡,不再触及潜意识,趋向正常状态,符合一种人格,这种人格不会因与潜意识对立而不发展,只会突破潜意识。这些潜在的精神病是心理治疗师的眼中钉,因为它们常常极难确诊。在这些情况下,理解梦境就尤为重要。
我们这就说到非专业分析这一问题。我支持非医学人士也学习并从事心理治疗,但若遇潜在的精神病时,他们可能容易出偏差。因此,我赞成非专业人士从事分析师的工作,但在专业医生的督导下,一旦有丝毫不肯定,就应向后者讨教。对医生而言,确诊并治疗潜在的精神分裂症常常就够困难了。对外行而言尤甚。但我一再体会到:非专业人士长年致力于心理治疗,并且自己也接受分析,略知一二而且也会一两手。再说,应用心理疗法的医生根本不够。此职业需要相当漫长而全面扎实的培训,需要全面广博的教育,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享有这些。
尤其若患者移情或者医患或多或少不自觉的认同大起作用,医患之间的关系偶尔可能导致心灵学性质的现象,我常有此经历。令人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病例,我使患者摆脱了精神性抑郁。此后,他返家结婚,但我不喜欢他妻子,初次见到她,就有瘆人的感觉。我觉察到,因为自己对她有影响,他对我心存感激,我就成了她的眼中钉。经常发生的是,妻子并非真爱丈夫,心怀嫉妒,破坏他与朋友的情谊。她们想要丈夫完全属于自己,因为她们不属于丈夫。妒忌的核心都是缺乏爱。
妻子的态度对那名患者就是难以应付的异常负担,在此压力下,婚后一年,他重新陷入抑郁。我预见到有此可能,曾与他约定,察觉情绪低落就立即联系我。但他没这么做,其妻不无推波助澜之举,她对他的意兴索然不以为意。他音信全无。
那时,我在B城做报告。午夜时分,我进了旅馆(做完报告之后,还与几名友人一同进餐),随即上床,但很久仍睡不着。将近两点(想必刚好入睡)惊醒,确信有人入室,还觉得好像门匆匆打开,马上开灯,但什么都没有,心想有人走错了门,就往走廊里瞧,可那里一片死寂。我想,“奇怪,确实有人入室了啊!”于是努力回忆,想起来因隐隐作痛而醒来,宛若某物碰到额头,然后撞到后脑勺上。——次日,收到一封电报,说那名患者吞枪自尽了,后来得知子弹卡在后脑勺上。
此处经历涉及道地的共时现象,在原型情境中(此处为死亡)并不罕见。通过潜意识中把时空相对化,我有可能感知其实全部发生在别处之事。集体无意识人所共同,它是古代所称“万物感应”的基础。在此病例中,我的潜意识知道患者的状况,整晚都觉得出奇的心神不定、烦躁不安,一反常态。
我从未试图让患者皈依,也不强加于人,一切取决于患者自己得出看法。在我这里,异教徒就是异教徒,基督徒就是基督徒,犹太人就是犹太人,命该如此。
我清楚记得一个丧失信仰的犹太女人。事情起于我的一个梦,梦中有一个不认识的少女来就诊,陈述病情,她一边讲,我一边想:我根本听不懂她的话。我不明白是什么事!可猛地想到,她有异乎寻常的恋父情结!——这是那个梦。
次日,我的日程上是四点时会诊,一个少女出现了,是个犹太人,银行主的富家女,俊俏、优雅、十分聪慧,已经接受了分析,但医生移情于她,最终恳求她别再去他那里,否则会毁了他的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