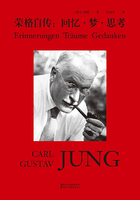
第13章 大学岁月(3)
大学岁月的头几年间,我发现,自然科学虽然促成无穷多的知识,但只促成寥寥无几的认识,而且主要是具有专门性质的认识。由于阅读哲学著作,我得知,不管怎样,心灵以事实为基础。若无心灵,则既无知识亦无认识,关于心灵根本就听不到什么,虽然处处不明言地假定有灵魂,但即使在提及它时,如在C.G.卡鲁斯那里,亦不真正了解,只有听起来如此这般的哲学思辨。我弄不懂这一奇怪的省察结果。
第二学期末,我的发现却后果严重,在同学之父——一名艺术史家的藏书中,我发现了60年代关于显灵的一本小书,是一名神学家撰写的关于招魂术起源的报告。最初的怀疑迅速烟消云散,因为我无奈地看到,基本就是自幼年起在乡间一再听说的相同或类似的故事。素材可靠无疑,但这些故事按自然规律也确有其事吗?尚无人确切回答这个巨大疑问。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看来地球上处处时时都一再谈到同样的故事,想必还是事出有因吧,绝不可能是到处有相同的宗教前提,情况显然并非如此,所以必定与人类灵魂的客观表现相关。但除了哲学家所言,恰恰根本无法查明这个主要问题,亦即心灵的客观秉性。
尽管觉得蹊跷、可疑,对我而言,对术士的观察还是关于客观心理现象的最初报告。诸如克尔讷和克鲁克斯这些人名令人印象深刻,我可谓遍览当时可到手的招魂文献。当然,我也跟同学们谈及此事,令人极为惊讶的是,他们有人的反应是嘲讽、不信;有的反应出忧心忡忡的抵触。一方面,我惊讶于他们可以言之凿凿地断言,不可能有诸如闹鬼和显灵转桌之事,所以,这些都是欺骗;另一方面,我惊异于他们的抵触似乎具有忧心忡忡的性质。这些报告是否绝对可靠,我虽也不能肯定,但到底为何就不会闹鬼呢?我们究竟从何得知,“不可能”有某事呢?尤其是忧心忡忡会意味着什么呢?我自己觉得这些可能性引人入胜、极富魅力,它们把我的生活装点得多姿多彩,世界增加了深度和层次。比如,为何做梦也会与精灵有关呢?康德的《视灵者之梦》来得正逢其时,不久,我也发现了在哲学上与心理学上评价这些理念的卡尔·迪普雷尔,发掘出了埃申迈尔、帕萨旺特、尤斯蒂努斯·克尔讷和格雷斯,阅读了斯维登堡七卷作品。
家母的二号人格对我的热情颇为认可,但周围其他人令人气馁。之前,我只是撞上传统观念这块绊脚石;现在却遇上强固如钢的先入之见,发现密友确实不会承认与众不同的可能性,他们觉得我的兴趣比我关注神学更加可疑!我感觉碰到世界边缘了,我最感兴趣之事,对别人而言云山雾罩,甚至是忧心忡忡的原因。
忧惧什么呢?我找不到对此的解释。或许有的事件逾越了时空和因果关系的有限范畴,这总不会是闻所未闻、惊天动地的吧?甚至确实有动物预知天气与地震,有梦境能预告某些人的死亡,有钟表在人死的瞬间停摆,有玻璃器皿在危急时刻破裂四散,这些事情在我迄今为止的世界里纯属理所当然。而现在,貌似我是唯一听说过此类事情者!我万般严肃地提问,究竟身陷何等世界。看来是都市世界,对乡间世界,对山脉、森林、百川、动物和上帝观念(可解读成植物和晶体)的现实世界一无所知。我觉得这种解释令人宽慰,无论如何,暂且增加了自信;因为我明白,虽然充满高深玄妙的知识,都市世界仍然眼界狭隘。这种洞见对我是危险的,因为它诱导人产生优越感、妄下雌黄、富于攻击性,招致别人理所当然对我反感。这些反感随后又带回了旧有的怀疑、自卑感和抑郁,我决定不惜代价中断这种恶性循环。我不想再遗世独立,落得怪人的污名。
通过医科预考之后,我成为解析室的助教,接下来的那个学期,解剖室主任甚至委托我主持组织学课程,当然令人志得意满。我当时主要关注进化论和比较解剖学,也了解了新活力论,最迷人的是广义上的形态学观点;不讨人喜欢的生理学让人极为厌恶,因为做活体解剖只是为了演示。恒温动物是我们的亲戚,绝不只是有脑的机械动物,我总也摆脱不了这种感觉,因此,只要有可能,就逃避这种演示。虽然我明白,人不得不在动物身上做实验,但仍觉得演示此类实验残暴可憎,关键是多余,仅凭描述,足以想象演示过程。我对受造物的同情绝非源于叔本华哲学中的佛风,而是更深刻地基于质朴的思想观点,也就是对动物有不自觉的认同,然而,当时对这种重要的心理状态浑然不觉,对生理学反感到在该科毕业考试中也乏善可陈,总算蒙混过关了。
后面几个临床教学学期排得满满当当,几乎无暇去偏僻地区远足,只能在周日钻研康德。我也热衷于阅读E.冯·哈特曼的作品。尼采列入计划已经有一阵子了,但我迟迟没有阅读他的书,因为自觉准备不足。当时,尼采广受议论,但多数人不接受他,对他议论最为激烈的是“内行的”哲学系学生,我由此推断出更上层的圈子群起抵制。雅各布·布尔克哈特当然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他散布针对尼采的好些批评意见。还有一些人认识尼采本人,所以能够说出他各种不甚合人意的怪事。他们多半也未读过他的什么书,因此,耽于表面易受误解之事,如他玩“绅士”把戏、弹钢琴时的做派、文笔夸张,纯属必定让当时的巴塞尔人心烦意乱的怪癖。这些事却不能充当我延迟阅读尼采作品的托辞(相反,它们本该成为最强烈的诱因),找的借口倒是暗自担忧,自己或许会与他相似,至少在“秘密”使他受周围的人孤立这点上。谁知道呢,或许他有过内心经历,有过洞见,不幸的是,他想言说而无人会意吧?显然,他格格不入或者至少被视为如此,被看成怪胎,我绝不想当这样的人,生怕可能认识到自己如尼采一样“也是孤家寡人”。当然,若能以小比大,他可是当教授,著书立说,也就是达到梦幻般的高度;他虽然出身神学门第,但身处辽阔疆域绵延至海的德国,而我只是个瑞士人,出自一个边境小村中简朴的牧师楼。他说一口文雅的标准德语,会拉丁语和希腊语,或许还有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而我只会还算熟练地使用瓦吉斯——巴塞尔德语。他拥有所有这些美事,毕竟有资本来点格格不入,但我可能跟他相似到何程度,不得而知。
虽有担心,我还是好奇,决定阅读他的作品。先抓到手的是《不合时宜的省察》,我出离兴奋,很快又读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9],就像歌德的《浮士德》一样是强烈无比的经历。查拉图斯特拉是尼采的浮士德,二号人格是我的查拉图斯特拉,然而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肯定,查拉图斯特拉是病态的。二号人格也是病态的?这种可能性令人胆战心惊,自己长期不愿承认这种惊恐,它却一再不合时宜地露头,让人应接不暇,迫使我反躬自省。尼采人过中年才发现生命中有二号人格,而我少年时代就了解二号人格。尼采幼稚冒失地言说这不可言传之事,仿佛一切正常,我却很快发觉自己吃了苦头。但另一方面,他天赋异禀,年纪轻轻就去巴塞尔担任教授,对面临什么一无所知。恰恰由于天赋过人,他确实应该及时觉察有什么不对劲。我想,他病态的误解就是,懵懵懂懂、毫无惧色地把二号人格放到世界上来,这个世界对此类事物一无所知、一窍不通。他幼稚可笑,满心希望有人会对他的心醉神迷深有同感并且理解“重估一切价值”,却只发现文化市侩,甚至富有悲剧意味的是,他本人就是其中之一,与他人一样不自知,埋头于奥秘与不可言说之事,想向遭众神抛弃的迟钝麻木人群夸耀这点,因而,语言夸张,比喻过度,狂热过分,徒劳地试图闻达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热衷于彼此无关的值得闻知之事。而他这个走钢丝者甚至还不能自控。他不了解这个世界——这个十全十美的世界,所以是走火入魔者,周围的人对他唯恐避之不及。在友人和熟人中,我只知有两人公开拥护尼采,均为同性恋,一人自行了断了,另一人因怀才不遇而落泊。面对查拉图斯特拉这个非凡之人,其他人绝非不知所措,而是简直波澜不惊。
《浮士德》给我打开一扇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又关上一扇门,这回关得严严实实,还是长期的。我就像老农,夜魔使计把两头奶牛塞到同一只笼头里,小儿子问,这样的事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他答道:“亨利,别说这个。”
我看清了,不说人所共知之事,就寸步难行。在此方面幼稚者不明白,说对方不知之事对别人意味着何种侮辱。人们只宽宥作家、记者或诗人有此类无良之举。我明白,只能通过事实传达新理念或哪怕只是不同寻常的视角。事实明摆着,不可能长期抹杀,有朝一日,会有人经过,知道发现了什么。我看出,由于没有上策,自己其实只是耍嘴皮子,而非拿出事实;自己完全缺乏事实;两手空空,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经验。我怪罪哲学家,他们说的都是人之经验所不及之事;而在本该对经验做出回应之处,他们处处沉默。我虽觉得也算某时某地穿过钻石谷,但无法使人信服自己带来的岩石样品与砾石有所不同,若细看起来,甚至说服不了自己。
1898年,我开始研究自己未来要从事的医生职业,很快认识到必须术有专攻。可以考虑的只有外科或者内科,由于在解剖学上受过专门的教育,而且偏爱病理解剖,我倾向于前者,若有所需资金,极有可能考虑以此为业。令人极其尴尬的是,要完成学业就不得不负债。我知道毕业考试后不得不尽快维持生计,所以设想在随便一家州立医院从助理医生起步,在那里比在专科医院、诊疗所更加有望获得有酬职业,但临床职业高度依赖上司的提携或者个人的好感。鉴于名声可疑、经常遭遇诧异,我就不敢想会走运,因而不奢求机会,至少落脚在一家地区医院当助理医生,其他的则取决于我是否勤奋、能干、中用。
暑假发生了将让我深受影响之事。一天,我坐在书房里研习教科书,隔壁房间的门半开半掩,家母坐着织毛活,那是我家的餐室,里面放着胡桃木圆餐桌,它是祖母的陪嫁品,当时约有七十年历史了。家母坐在窗边,离桌约一米远。妹妹在学校里,我家的女仆在厨房。突然一声爆响,像手枪在射击。我一跃而起,冲入听到爆炸声的邻室,家母失魂落魄地坐在高背扶手椅里,编结物从手中落下。她结结巴巴地说:“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正好在我边上——”一边朝桌子看去。我们看到桌面开裂过半,绝不只在胶合处,而是穿过自然长成的木头。我哑口无言,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在我们这里,夏日通常湿度很高,自然长成的木头风干七十年,一天就爆裂了?又不是干冷冬日在生火的炉边!此类爆炸的原因究竟会是什么呢?我想,总会有奇特的巧合吧。家母点头,用二号人格的声音说:“对,对,这预示着什么。”此事给我留下了可憎的印象,很恼火对此无话可说。
约十四天后,我晚上六点回家,发现全家,亦即家母、十四岁的舍妹和女仆紧张不安。约一小时前,又是震耳欲聋的一声枪响,这次不是已经受损的桌子,爆响来自碗柜,那是一件19世纪初的笨重家具。她们四下找过,但没有发现一处裂缝。
我马上开始把碗柜及其附近找了个遍,同样毫无结果,接着搜遍碗柜内部和所放物品,在放面包筐的抽屉里,发现了长条面包,边上是切面包刀,刀刃折断过半,刀把躺在方筐一角,其他三角各有一片刀刃。四点喝咖啡时,还用过刀子,过后放起来了,没人再动过碗柜。